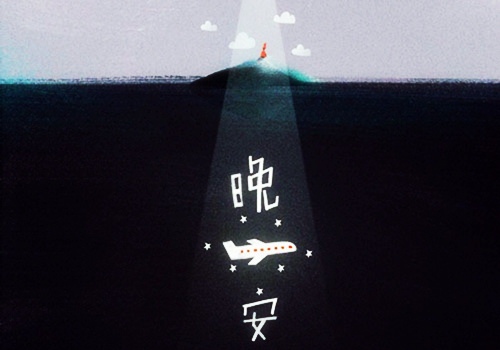“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 转眼就到二十三”。在鲁中钢城艾山一带每到腊月初,十里八村便陆陆续续听见猪的嚎叫声,一年一度的杀年猪,从此开始,虽然离年还有段日子。但备年货、杀年猪便开始了。尽管现在杀猪卖肉都集中到屠宰场,但民风淳朴的村民还仍任保持着杀年猪习俗,可见民风民俗的魅力成为一种习惯。
“寒冬腊月天,是水冻成团”。这个时候猪毛开始发刺,有经验的家庭主妇就知道,即使喂得再好,猪也不会上膘,便选个家里人齐全的日子,找来村里杀猪的,烧了一大锅开水,逮猪,一刀见血,吹气、褪毛,分割肉。早有一群人等在饭桌旁,看似闲聊,嘴里一个劲儿吞咽唾沫,厨房里云遮雾绕,不时飘来的屡屡肉香,那是极大的诱惑。小孩子最盼着杀猪。全家人苦熬一年,肚子里早没了油水,杀猪又何尝不是为了一饱口福。
童年时,最期盼的那当然是过年了,过年不仅能吃肉吃鱼,还能穿新衣。劳动积极性也是空前的高涨。大人吩咐到邻居家借盆、板凳,那是一个乐此不疲。这个时候,在厨房里忙活的娘,向我们传达父亲的旨意,小声告诉我们叫大爷、二叔到我们家里来帮忙和喝酒吃肉。之所以这么神秘,是怕得罪没有被邀请的人。农村有个习俗,杀年猪请人吃饭,主要是请家族近枝的叔叔、大爷;平时日子过的紧吧,大家都忙各的也没有时间聚,过年了也农闲了,大有借客杀鸡的味道。因此,村民便有了那句“大年午静吃包子,没有外人”的俗语。
淳朴的村民,用淳朴的方式延续传统,也不乏小市民的胸怀,有时想想感到挺可笑的。平时舍不得奢侈,这个时候可以大方一回。肥肠、猪肝、舌条、猪肚子,猪蹄子、猪耳朵;光猪身上的就能炒六个菜,再炖上一锅猪肉白菜粉条就是一桌丰盛的家宴。因平时人们很难动荤,所以这一顿饭下来,总有几个喝高的人,迟迟不肯离去,大呼小叫,猜拳行令,并招呼厨房里忙着的.母亲,再炒些青菜来。
在族人酒足饭饱离开后,母亲把肉一块块分割后浇上水冷冻,让二哥、三个放在抬筐里,用绳子拴住后,放到天井里的井里储存,一边把猪镖子、花油放进锅里,熬油,从邻居家借来的盆碗、桌凳,要送回去,为了不白用人家的还要压上一块或两块冷却的猪血,在那个时候这是稀罕物。
母亲安排我们的活路干完后,便出去玩耍,吃得好,心情也好,满山村跑一个晚上,也不觉得累。天上出了星星,玩心未尽的才回家睡觉。一开房门,满屋子的香味,刚好因玩耍肚子有点饿了,饿虫在肚子里蠕动。油猪罗梭已经出锅,母亲放上了细盐,不咸不淡,空口吃也好,就着煎饼吃也行。
但我有我自己独特的吃法。盛一碗米饭,白天客人吃剩的菜汤晚上静已经冷凝,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的大油,把它泡到米饭里,拌着吃,特别香。直吃的打‘饱嗝’,嗝一口气都满嘴透着氲氲的猪肉味。
下到井里的肉等到过年时才能再吃。一个正月,客来客往,到了二月二,一个肥猪早已“蚕食”完毕,想要吃肉,要等到明年。觉得那时候的猪肉好吃,窃以为和漫长的等待有直接关系。
俗话说,过年容易春难挨。从正月到五月,整整半年,不仅很难吃上猪肉,就普通的青菜也很难吃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全村能杀五六头猪就算不错,到了80年代是两家合杀一头,到九十年代中期,养猪、杀猪自由,想吃纤维粗的猪肉,自己喂一头,过年杀了。虽然不再像60年代那么稀罕,但吃来也有滋有味,氛围里氤氲了热闹、和睦和义气。
现在的猪都集中屠宰了,多是饲料喂养的没了故乡草黑猪的那种特有的结实。现在人们也注重养生了,什么吃猪肉会得高血压、血脂稠、血糖高等,吃猪肉也不再那么贪婪。尽管每年都会回故乡过年,但旧时故乡乡人杀猪时那浓浓的年味以及邻里间的那种和睦还是深藏在记忆深处的。
我早早就起来烧了两大锅开水,爱人找杀猪的屠夫去了。说是屠夫其实不是专业杀猪的,只是敢下手,年年过年时帮村民杀几个猪。按辈分论从屠夫叫大叔,爱人和大叔一起进来院子,我开门迎了出去,接过大叔挎着的布袋子,里面装着杀猪刀,刮子,和大砍刀。我放在了外面的桌子上。
门开着,门口喷出一团团的`热气,锅里的水翻开着,灶膛里的松木劈材燃的很旺,松树油发出吱啦吱啦的响声。屯里的亲友和邻居都来帮杀猪了,几个人从猪圈里 拽出猪七手八脚的把猪压倒在桌子上,杀猪大叔嘴里叼着烟,脚上穿着水靴,腰上系一条胶皮围裙,袖子卷的老高,手握着刀,等着大伙把猪按好,几个人按着猪,大叔用舌头尖喷掉还没燃尽的烟头,喊了一声;接血,表弟一手拿盆一手拿两根黍杆棍,等着接血,只见大叔用刀背在猪脖子上蹭了几下,一刀捅进去,一抽刀一股血喷了出来,猪哼哼着四蹄抽动表弟一面接血一面用黍杆搅动,猪颤抖了一阵不动了,接了大半盆血。大伙撒了手,大叔直起了腰,沾满血的双手在围裙上抹了几下,又抽起了烟。
有人从屋里往外面一桶一桶的提开水往猪身上到,另几个人拽腿的,薅尾巴的,反过来倒过去 ,一会浇完了,两三个人开始刮毛猪毛刮完了,大叔随手拿起院里的半块砖在猪身上蹭全身都蹭到了,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房檐戳了一根梯子,用来挂猪的,大叔在猪后腿处扎了一个窟窿,几个人抬起猪大腿窟窿挂在了梯子秤上,只见大叔拿着杀猪刀在猪脖子上划了一圈,把刀放下,双手攥住猪耳朵一宁猪头就下了了。开始开膛,取心肝肺,肠子,摘油洗肠子一阵忙乱,肉也剁成了三五斤大小一块,摆在房顶上的黍杆帘上,等着冻了,好放在缸里。
灶膛里的火仍在燃烧着,锅里炖着杀猪菜,又往锅里三十多斤肉,慢慢的炖着。
这时人们闲了一会,开始喋喋不休的议论着现在猪的行情,猪肉的好坏,一个说;咱吃的肉长一年了就是香,那个说卖的猪都是激素吹得四个月就出栏,肉滑不溜的都让有钱人吃了,又说猪吃完料就睡觉,人吃了脑子都笨……。从谈猪又谈到养猪污染环境,有的说离猪圈近的井水不能吃了,那个说前院一冲猪圈满屯都是臭水,大伙你一言我一语的唠着……。
做了一个多小时,肉好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做了两大桌子,大盘的猪肉,大碗的猪血,热气腾腾的酸菜汤,端在桌上,人们喝着酒,吃着肉,说着唠着其乐融融。
好文者也就用键盘记录下了这杀年猪的经过。
听同事们在一起议论家里包了多少粘豆包,做了多少冻豆腐,杀没杀年猪,我随意翻看下日历,时间已经跨进了腊月。腊月里“杀猪,淘米,做豆腐”,这个风俗习惯在我的家乡已经延续了千百年,就像春天要播种一样被列为一年当中必做的大事。
小时候,我们家虽然没有像乡下人那样在腊月里做豆腐,但淘米包粘豆包每年还是会如期进行的。至于杀年猪,其实是凤毛麟角。偶见的几次杀年猪,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六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腊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同学放学路过邻居家,看到他家院子里的桌子上捆绑着一头肥头大耳的大黑猪,“吱吱哇哇”嚎叫着,拼命挣扎着。出于好奇,我们几个孩子便在一旁围观,眼看着杀猪师傅庖丁解牛般分解完整头猪,耳朵边夹着洋烟,手里拎着块猪肉,嘴里哼着小曲离开了院子,却始终没看到有人来邻居家买猪肉。原来,人家杀的那头年猪,一两肉都没有往外卖,全都留作自家吃,荤油还炼了一整坛。这事一传俩,俩传仨,邻居家杀猪不卖肉、大富户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县城。这消息也令我震惊,羡慕人家的同时也梦想着自己家里杀一头年猪。
两年后,我们搬了家,有了独立的一个小院。爸就在院子里砌了个猪圈,抓了一头小猪崽来喂养。从那以后,家里淘米积攒下来的泔水不再朝外卖了,妈还买来点豆饼当细粮,泡水喂给小猪崽吃。眼瞅着小猪崽一天天长大,食量也大了起来,自家那点淘米泔水根本不够她吃。没办法,爸和妈就给我们几个孩子定了任务,每天放学后都要去挖野菜,割猪草。
那时候城郊的田园都是生产队的,不允许外人擅自闯入偷挖野菜和割草。为了完成任务,我就和住在城郊的同学拉关系,让他们带着我混进田园去挖野菜、割猪草。有一天,为了抄近道回家,我挎着一篮子野菜来到护城河边,挽起裤腿,拎着鞋子和菜筐下了河。倒霉的我脚下一滑,人就漂在了水面上。拼命挣扎了好一阵,总算大难不死,在水中站稳了脚,可辛苦挖来的一筐野菜却早已逃之夭夭、付之东流了。我难过地抹了一把眼泪,爬上岸,又折返回去,重新割了一筐猪草回了家。
给猪挖野菜的差事是辛苦的,但当我看着那头小猪崽渐渐长得膀大腰圆、走起路来左摇右晃的时候,我知道离心中的'那个梦想,那个盼头已经很近了,也就忘记了所经历的艰辛。
日月如梭,转眼进入了腊月。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吱吱哇哇”的猪叫声惊醒。当我爬起身来,穿衣下地,来到院子里的时候,爸和请来的杀猪师傅已经将那头滚瓜溜圆的大肥猪捆绑得结结实实了。大肥猪极不情愿地蹬踹着,嘴里不停地哼哼着,吼叫着。杀猪师傅拿下了叼在嘴上的那把雪亮尖刀,对准了肥猪的脖子。此刻,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日久天长与肥猪接触,给她添草喂食,看着她成长,心里已经与她产生了莫名的情感,我不忍看着那把尖刀捅进她的脖子,转身跑回了屋里。我紧紧捂住了耳朵,害怕听到她求生的哀嚎。我紧闭上双眼,恐惧看着她在痛苦挣扎中死去。
等我将两手从耳朵旁拿开的时候,外面早已恢复了平静。我扒着玻璃窗户向外看,桌子上的猪肉已经所剩无几,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手里拎着余温未散的鲜猪肉,喜笑颜开地离开我家的院子。这时候,我隐约听到妈对爸说,留下几斤肉吧,孩子们都熬苦了一大年了,早就像小燕子一样张着嘴盼着吃上一口自家养的年猪肉呢。爸听完妈说的话以后,看了看手中攥着的一沓钱,迟疑了一下,然后冲着妈点了点头。
妈用留下来的猪肉给我们做了一顿杀猪菜,算是圆了我们的梦。当妈揭开煮肉锅的那一刻,年猪肉的香味四溢,扑鼻而来,直刺味蕾,馋得我垂涎欲滴,迫不及待地在锅里捞起一块肉,扔进嘴里。妈笑着说,慢着点,别烫着,锅里还有都是呢。爸问我,肉……香不?我嘴里咀嚼着喷喷香的猪肉,回答爸说,香,真香。
那是我记忆中吃到的第一块自家杀的年猪肉,那种独特的肉香至今仍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