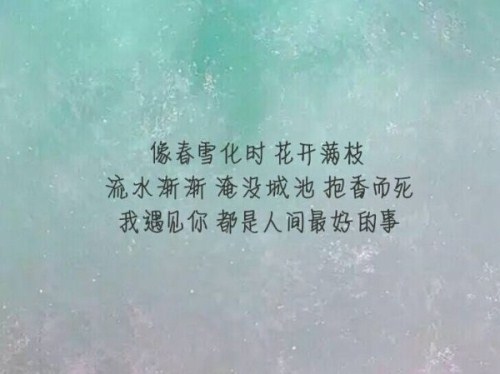光中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文学大师,这次携夫人赶赴祖国大陆专程是为参加他的母校——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5月17日下午,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的时候,我在南大西苑见到了他和他夫人。采访间,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他不顾旅途疲惫,依然谈笑风生,博古引今,睿智和真诚在话语间处处显现。
何晴:余教授,众所周知,您曾在内地、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地都居住过,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也曾把您居住过的各地作比,而祖国大陆就像是您的母亲,那么南京在您的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余光中:首先要声明,我是南京人。因为我出生在南京嘛,南京是我生命的起点,是一切回忆的源头啊。而且我在南京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从我1928年出生到1937年,我都一直住在南京。所以我的童年时代差不多都在南京度过的,也是在南京读的小学。中学是在四川读的,为什么在四川读书呢?因为抗日战争中学从南京搬到后方去了,我记得那个中学叫做南京青年会中学。战后我随中学回到南京,高中毕业后,后来我又读了金陵大学。我在南京不但住了这么久,而且是出生地,而且是在这里接受的教育,所以南京对我一生影响是特别深的。
何晴:您曾在各地的多所大学就读和任教,您认为您当年就读的金陵大学,也是现在的南大,对您后来的成就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吗?
余光中:那时侯我还小呢,也就是懵懂,那个时候我读的是外文系,当时属于文学院,当然对我的英文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对我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但是大学,还有整个南京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玄武湖和紫金山,我读大学先住在鼓楼,后来搬到城西北面去。
何晴:您在一篇著名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中表达了对4个女儿真切的关爱,你能否谈谈作为父亲在女儿成长中的心理的变化。
余光中:对,我们家有4个女儿,她们小时侯是最可爱的,在十六七岁以前完全属于父母,完全属于爸爸,所以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小木屐》,在南京穿木屐的比较少,在台湾尤其以前大家都穿木屐,我的小女儿穿着木屐刚会走路,踢踢踏踏,那我就蹲下来张开两臂鼓励她向我走来,那时她就孤注一掷地向我跑来,因为那时候在她生命中惟一的男人就是她爸爸。可是过了那个年龄就不一样了,我只看到她的背影了,没有看到她向我奔来的样子,因为男友在门口按铃。而她冲出去的速度之快,而且不再穿小木屐了,是穿高跟鞋。她们4个人我也写了你说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就是4个地下工作者,背着我来追求我们家的4个女儿。而且我最不利的一点呢,是她们的妈妈还站在她们的那边,里应外合,所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昏君”了。我希望我的4个假想敌写写情书,可以锻炼中文,顺便也可以让我看看他们的文笔如何,可是他们总是打电话,那么我也听不到了,其中的玄妙我也不懂,并且荒废了中文。所以伟大的情书已经成为绝响了。因为电话就装在我的书房里,一到晚上电话就来了,我家有5个女人,每个人要是有3个电话,我每晚就要接15个电话,都快成为接线生了。(笑)
何晴:我们都知道您与您的夫人白头偕老,可以说生活安定幸福。您对这种生活态度解释为,您用您的天才来写作,而日子过得去就行了。是否正是这种安稳的家庭生活给您的写作创造了稳定的环境?或者,它有时候是否也会局限您的创作灵感?
余光中:要说安定,我少年时代很不安定,因此我才会读3所大学,这意味着战乱使我不能在同一个大学读完,所以少年时代应该说非常动乱的,倒是我去台湾之后生活才显得安定。至于说幸福就很难说了,也有苦日子。后来的安定生活是给写作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
许多人都认为诗人多情,情感丰富,其实感情丰富的人多得很,诗人也不一定非要多情,家庭生活是不会局限我的灵感的。至于灵感,它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也是来源于生活的。灵感这个字眼应该最初是从国外来的,也就是“inspirition”。所以梁启超当年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干脆翻译成“因斯皮里纯”。可见没有一个定理。现在都统称为“灵感”。有人认为灵感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写不出来就怪灵感。其实我觉得灵感是一位艺术家或者科学家对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他经常思考,想多了这个问题甚至进入他的潜意识,做梦也在经营,散步也在思考,直到最后豁然贯通,那一刻如有神助,我们把它叫做灵感。其实灵感是不断思考、不断体会之后忽然没有障碍了,想通了,问题很透明地呈现在你的面前,是不断努力的结果。因此灵感绝对不会来拜访懒惰的人。如果没有事先的准备和思考,灵感恐怕不会来。如果没有艺术的修养、技巧的锻炼,就算创意来的那一刻,他觉得灵光一闪,可是仍抓不住。就像凡高,他在画家中也算是早熟的,他画画只有10年的工夫,从27岁到37岁,可是他也苦练了很久,临古人的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才画出像《向日葵》、《星光夜》等许多杰作。他的画现在大家都很喜爱,但在他的生前他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一个画家,没人欣赏他,没人买他的画,甚至没有人爱他。所以,灵感并不一定需要丰富的感情经历,也不一定要尝试动乱的生活。
何晴:您是一个诗人,而在现实中您是如何用诗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
余光中: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要有诗,不过诗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人要过诗意的富有灵感的生活也不一定要做诗人。生活里面光有真理,有美德还不够,好像还缺少什么。生活里面还应该有艺术,不管是诗、绘画、音乐或者是雕塑,总而言之,生活里面应该有美。有一位美国的亿万富翁,他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有一天他看到小女儿带笑地走过来,心花怒放,那一刻他就想做个诗人,可是他想不起如何形容他的女儿多么可爱,他想了半天说,啊,你美丽得像一张百万元的大钞。那就是说一个人虽然很富有,可是在诗意生活上可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因为没有想象,连赞美女儿也想不出一句诗来,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所以美是不能量化的,它是一种质,不是一种量。所以王尔德说,现在人的毛病就是什么东西都知道它的价格,可是没有东西你能知道它的价值。
何晴:您被称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40余种作品集。而在祖国大陆,您的诗歌似乎名声更盛,一首《乡愁》至今仍被引为经典。而您自己认为,您最喜欢的和实际成就最大的创作体裁是哪一种?或者说哪种文体创作给你带来更多的收获?
余光中:我想祖国大陆很多读者都读过或者会背《乡愁》那首诗,不过我在大陆出版了二三十本书大部分还是散文,出的散文书还是比诗集多一点。我想大陆的读者读我散文的可能比读诗的多。诗、散文、评论和翻译这四样体裁我都蛮喜欢的。有时候碰到这一方面比较不畅顺的时候,就去经营另一方面,四样换着写。
何晴:请问您是怎样看待翻译的?或者您的翻译观是什么?
余光中:翻译吧,希腊神话中有9个姐妹,nine muses做文艺女神。文艺女神当然可以给诗人激励和灵感的,9个缪斯,有的甚至还管到了历史、天文,当然更多的管抒情诗、情诗、史诗等等,我说过惟独没有缪斯来培植翻译,所以我说如果让我来创造,我要创造the tenth muse,第十个缪斯专门扶植翻译。因为翻译是门艺术,一般的艺术家像诗人只要把他能够写得好的东西写好就行了,而翻译家呢要把人家写好的东西过渡到另一种语言里去。一般的艺术家要有创造力,可是翻译家还要有适应力,别人的东西怎么样把它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我翻译过王尔德的3本喜剧,他是英国唯美派的大师,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的戏剧很难翻译,特别是台词,唇枪舌剑,很犀利。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报告说我怎么翻译王尔德的,最后一段我说道,王尔德是不好翻,我翻过来的中文打七八折,但有时候碰巧呢,我的译文比他的原文更好。那些与会者本来没有注意听,一听到这句话都觉得我这个人很自负,我说当然喽,王尔德的句子喜欢用对仗,对仗是中文最了不起的,因为中文是单音节对仗比英文方便,所以我一碰到他的对仗翻译成中文后就比他漂亮。不是我比他高明,是中文在这一点上比英文高明。
何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您是受到了冲击还是启发?为什么您在西方生活那么多年还是认为中国语言不能西化?
余光中:冲击和启发两者都有,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中国文学、传统文化影响最大,中国作家一定要认清两个传统,一个是诗经的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对作家帮助很大。不过西方文学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提供给我另外一种观点和角度。中国文学受西方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能够常葆纯粹,特别是语文的优越性。所有的语文跟钱币一样都要跟外币交流,而且其交流的情况跟货币的比值比起来复杂得多。其实中文很早就受到外来的影响。而现在影响我们最大的外文,就是英文。英文和中文开始交流的时候,英国人学中文的不多,中国人学英文的多。但许多社会科学的名词最初都是日本先翻译的,中国再翻过来的。许多难以翻译的名词就用声音解决,比如“坦克”“引擎”“作秀”,有些词一直沿用下来。所以世界上语文是很难保持其纯粹的,通过与外文交流以后多少会改变其面貌。
中文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美丽的文字,不能到了一个程度反而把中国的文学给抛掉了,或者中文跟着英文走,很西化。这些都不是好趋势,应该引起中国读书人的警觉。我在大学毕业后两年曾经把《凡高传》翻译成中文,30多万字,过了20年,又有出版社要出新版叫我来修正。结果我修正又花了一年,当初翻译也才花一年,我修订了两万处。倒不是因为我当时的英文很差劲有误解,我改那么多处是改我的中文,我现在的中文已经不像当年因猛读英文而把英文的习惯带到中文里来那样比较西化了。我现在不满意那种写法,所以把它洗一遍。林语堂先生生前和我讲过,有人盗用他的书他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生没有用“人们”这两个字,他说“人”变为复数加个“们”这不是中文,所以他只用“世人”“人人”“大家”。中文西化也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善性西化,一个是恶性西化,这其中有成王败寇的区别。举徐志摩的`诗《偶然》为例,他走了一步险棋,但字句欧化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善性西化。
何晴:您怎样评价中国新诗发展的100年历程?您认为对新诗做过贡献的诗人除了您还有哪些?
余光中:中国新诗的100年有很多好诗,也有很多好的诗人,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现在名家辈出。早年不用说了,像闻一多、徐志摩这些人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后来呢,像40年代的卞之琳就很好,他是很细腻的一位诗人。还有冯至,诗中很有哲理。而目前硕果仅存的两位,一位就是辛笛,他目前在上海,另外一位就是臧克家了,好多年没有写了。这两位都很好。像年轻一代杰出的诗人有舒婷、北岛。
何晴:您认为诗歌创作有技巧可言吗?要是有的话,您认为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余光中:其实诗歌创作的许多技巧都和同情、想象力有关系,比如说夸张,“海上的浪像山一样高,那就是把浪跟浪连在一起。”不过这个想象力很低级。那么一个人对别人有同情,对万物有同情和共鸣,这样自然就接近一个诗人了,你的心底就能和万物沟通。就像诗歌里面的很多技巧,像明喻、暗喻、夸张、象征等都和诗人的同情、想象力有关系。所以要用同情、想象力和广泛的好奇来看万事万物。雪莱说的好,“科学重万物之异,艺术重万物之同。”能在万物之间找到相同的一点就能有诗意,就是一个诗人了。
何晴:您一直在通过文学来促进两岸和平,您认为两岸文化差异在什么地方?
余光中: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问题。两岸文化说不上有差异,因为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就是政治情况不一样,文化的源流还是一样的。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无论是做学问,无论是写作,无论在哪一岸,甚至于在香港,或者你是一个华人在南洋吧,或者你是一个留学生在欧美吧,只要你是一个华人,那你要做一个学者或者做一个作家,一定要认识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华文学的大传统,那就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另一个是小传统,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的传统。一个中国作家要是不知道这两种传统,那是不可能的。两岸其实都是继承了这两个传统。像台湾最崇拜的一个神叫妈祖,妈祖就是福建人,她在海上救人,她成为台湾海峡的守护神,她就是福建来的并不是台湾本身的。他每年过年也是过中国年,他也要过中秋也要过端午,他中秋也要赏月,他元宵节也赏灯,他骂人还是用中国话。所以没有两岸文化的不同,绝对文化的不同,就算是文化表面上的若干现象不同,其实也是短期政治的分离的后果。所以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为了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了五千年的文化。”
台湾早年对于美国文化的吸收,对于英文的重视,现在大陆也在这么做。当然把它当做世界化的一个阶段未尝不可,不过除了世界化之外,我想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也要有历史感。世界化是一个横的宏观,历史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了解,应该是一个纵的宏观。这两个宏观都是中国读书人必须修炼的美德。
何晴:您的诗作《珍珠项链》对您和您夫人婚姻生活有什么寓意吗?
余光中:我写给夫人那首《珍珠项链》正值我们结婚30周年,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是1986年。因为30年的婚姻按照西方的说法是珍珠婚,以买珍珠来纪念。所以我们经过香港的时候就进了一家珠宝店,店里的女孩就拿来一个盘子,托着18寸长的珍珠项链说,这个很不错。可是我后来又想,30年只有18寸,一寸光阴好贵啊。
因为珍珠是圆的,让我想起晴天的露珠,雨天的雨珠,两个人分开的念珠。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是有晴又有雨的,有幸福又有迷茫。
何晴:您对当代大学生的恋爱怎么看?
余光中:我觉得你们不要因为面对爱情将来可能的迷茫迟疑不决,你现在要追求幸福就尽管去追求幸福,不要担心将来有幸福还是迷茫。有人说“只要青春不要痘”,事实上你选择了青春也就要接受青春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