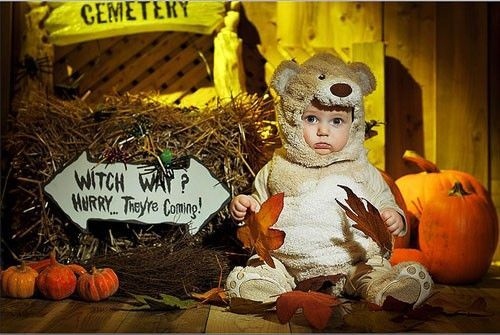
无聊的我打开了QQ音乐,听了几段90年代的流行歌曲,我跟着歌曲中的节奏陶醉忘情,那时候的歌曲是朴实无华实实在在的侵入肺腑,我最喜欢听陈红唱的常回家看看,那歌中的词句让人感到特别的温暖。毛阿敏唱的篱笆墙的影子,还有那英唱的山不转水转等等等等,这些歌都让我听的如痴如醉。尤其是当我听到解小东唱中国娃的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这句词就像是回忆器一样,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因为我就是穿着妈妈纳的千层底长大的。
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春夏秋冬穿的鞋都出自我母亲的那灵巧的双手,在我刚刚记事起就常看见母亲盘着腿坐在炕上,嘴里一边给我们姐弟两个讲着童话故事,一边右手抻着麻绳线,左手握着鞋底飞针走线的给我们做着新鞋。她手里的动作加上她嘴里的故事,好像是母亲在给我们说评书,我们两个小观众静静的听着很入神。
据母亲讲;母亲在7,8岁的时候就跟着姥姥学针线活,那时候的女孩子没有现在的女孩子们有福气,能每天无忧无虑的上学。姥姥家里一直很穷,没有钱让母亲上学,再者老封建的人们不让女孩子上学,只有乖乖巧巧的学做针线活,给自己将来找婆家打基础。就这样母亲在姥姥的调教下,白天和姥爷去庄稼田里干活,晚上对着煤油灯学做针线活。小小的年龄早早就学会了怎样操持家务。
母亲在18岁的时候嫁给父亲的,出嫁的时候,姥爷姥姥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给母亲做陪嫁,她随身的陪嫁就是有一双会做针线活的巧手。
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穿的是手做的鞋,根本没有钱去买鞋穿。母亲就一年到底不歇息的做鞋,那个时候不管是哪一家,都有做鞋用的.麻皮。母亲有空闲的时候就用家里的麻皮打麻绳线。家里有一个打麻绳线用的两边宽圆,中间细的脖吊儿,是用木头做的,上面有一个铁钩,母亲把麻皮绕在脖吊儿上,然后用手把脖吊儿一转,那脖吊儿就突突的旋转了起来,就像是孩子们手里玩的陀螺和风轮一样,旋转的特别快,那麻皮自然就被这脖吊儿给拧成了麻绳线了。我和弟弟在一边静静的看着母亲就像变魔术一样,一会的功夫就打出了那么多的麻绳线。
麻绳线准备好了就该准备鞋料了,母亲从柜子里面取出一包烂布头来。现在想起来,当初那是什么烂布头啊,连现在的垃圾都不如,布块最大的就是巴掌大,而且质量还是大窟窿小眼睛的不耐用,连指甲盖大的小布块,母亲看了都是宝贝舍不得扔掉。母亲先用一点白面做成稀稀的浆糊,然后找来一张破报纸,在上面刷好了浆糊,然后就是把那些小的不能在小的布块,一块紧挨一块的粘贴在上面,一层浆糊一层布块,那零零碎碎的小布块在母亲的巧手摆弄下,块块层层粘贴的是那么的均匀。
半天的时间过去了,母亲已经粘贴了好几张像纸箱子一样厚度的布苔,然后再把它们贴在院子的墙上让太阳晒着,等一两天晒干了以后。母亲就按照我们家四口人脚上的尺码开始做鞋了。首先把先做好的鞋底样儿在石板的下面再压上几天,说这样压出来的鞋底子结实耐用的。
几天以后鞋的各种工作都准备就绪。母亲开始纳鞋底儿了,她先用针锥子在鞋底儿上“开道”,然后再用大眼针带着麻绳线在后面通过,就这样一针针一线线的不停的飞梭,母亲不知道做了多少双冬天的棉鞋和夏天的布鞋。久而久之母亲常拿针锥的右手托上聚成了厚厚的一块硬茧。
有句古话说的很现实:洗手做鞋泥里踩,这句话在我们姐弟两个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母亲辛辛苦苦给我们做好的鞋,我们穿上以后还没有新鲜半天,就把它改变的面目全非了。弟弟的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勾破了一个三角口子,我和小朋友踩踏河上的冰水,把一双干干净净红底黑花的条绒鞋,一瞬间弄得成了泥鞋了。在那个天真无邪的年龄里,我们哪能够理解母亲做鞋的辛苦呢。
岁月热心的伴着母亲手里的脖吊儿飞转着,母亲的青春也随着那飞转的脖吊儿和纳鞋底抽拉的麻绳线悄然而逝。母亲辛辛苦苦的用她那灵巧的双手打扮着家里的一切,不管家里有多穷,那怕是补丁摞补丁,我们大人小孩都是穿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和弟弟随着母亲那脖吊儿的飞转也长到17,8岁了。年龄长了人也懂的俏色了。那时候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已经开始买鞋穿了,我看见和我同龄的孩子们脚上都在“更新”。我自己的脚还是“原型照旧”,在同学们面前很是“抬不起头来”。所以我每天下了课回到家以后,就软磨硬泡的缠着母亲给我买鞋穿。
时代的变化,让一天比一天苍老的母亲不得不从那旋转的脖吊儿中解放出来。岁月的飞刀很“亲切”的在母亲的双鬓上镶上了摘不去的霜花,但是永远改变不了母亲那勤俭节约的性格。母亲那布满硬茧和深沟的双手,刻印着她一生中经历了多少的坎坷和苦难,那一只只鞋底就像是一张张书笺,又写满了多少母亲的艰辛录迹和对儿女们的无限牵挂。当母亲看见她的孙子辈们穿的从商店买的鞋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的说:奶奶老了做不了了,要不然奶奶给宝贝们做的鞋不比买的差,那样就不用去花那冤枉钱了。
母亲风烛残年的瘦影就像是末秋的一片枫叶,在夕阳的拥吻下,摇摇欲坠。她颤颤巍巍的“叩着”暮日的“门闩”,总结了一生的成绩向大地做着汇报,大地敞开宽厚的胸怀,不征求我们任何人的意见,就把这个一世善良和满身苍桑的“孩子”接回了“家中”。
多少年过去了,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不管是晚秋的“拐杖”,还是初春的“嫩芽”,穿得戴得都是应有尽有。各个商店时尚的鞋种是琳琅满目任意挑选。现在不管走到哪里再也看不到打麻绳和纳鞋底的人了。那妈妈纳的千层底鞋在解小东的歌声中成了永远的回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总有一双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温暖着我的双脚。那时候,我们家在农村,买不起城里人才穿得起的皮鞋、球鞋和塑料底的布鞋。我们姐妹七个脚上穿的都是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一年四季我们总是看见母亲在纳鞋底,以至于如今我只要想起母亲,就想起她坐在炕沿上纳鞋底的模样,她一手拿着鞋底,一手拿着锥子和针线,扎一个眼,引一下线,吱儿吱儿地纳鞋底,不时还把针在头发上抹一抹。
做千层底布鞋是很费时费力的事情。为了制作千层底布鞋,母亲总是在平时就非常注意搜集碎布头,给我们做新衣服的时候,裁剪下的碎布头她要留起来;拆旧衣服的时候,把结实的碎布头留下来。这些碎布头都是母亲用来制作千层底布鞋的原材料。她把这些碎布头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包袱里。做千层底布鞋,最讲究的就是鞋底的制作。每到做鞋底的时候,母亲总是把平时积攒下的碎布头都找出来,然后用面粉煮一锅浆糊,再拿一块面板或者是吃饭的小炕桌。这时候母亲就开始工作了。她把浆糊抹在面板上,然后粘上一层布。再抹上一层浆糊,再粘上一层布。反复多次,就制作成了一块多层碎步黏在一起的布板。母亲叫它“疙把”。做好的“疙把”不能马上使用,要放在太阳地晒上三天。晒干了,晒透了,这时候“疙把”就变成了硬的。就像硬纸板一样。母亲小心地把它揭下来,作为半成品放在一边。
这时候,母亲比量着我们的脚,剪裁一个脚印的样子。母亲叫它鞋样。比着这个鞋样剪裁“疙把”,就把新作的“疙把”剪裁成了鞋样。这些鞋样摞起来就是千层底的模板了。这时候母亲就搓麻绳,用麻绳纳鞋底,把千层底的鞋子模板上纳满了密密麻麻的麻绳。千层底才算完成了。有时候,为了穿着漂亮,还要在鞋底的边沿部位表上一圈白布条。这样做成的鞋是黑鞋白底十分美观。用这样的千层底做得布鞋,就是千层底布鞋了。
做千层底的布鞋最费力气的是纳鞋底,母亲长期纳鞋底,劳累过度得了肩周炎,一到晚上就疼得钻心,睡觉都困难。白天还要继续纳鞋底。因为那样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我穿两个月就坏了,这倒不是母亲做的鞋不结实,而是我们的活动量实在太大了。弟弟们要穿着这样的鞋踢足球;我要穿着它跳皮筋、跳绳、踢毽子。而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仅仅是纳鞋底就把母亲累坏了。何况母亲每天除了纳鞋底还要做饭,洗衣服,缝制衣服,补补丁,织毛衣等等。我想:假如母亲做的这一切都是需要儿女支付工资的,那么哪个儿女能付得起清啊?
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美观大方、穿着舒服,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最爱。这种布鞋夏天穿不臭脚,不出脚汗。冬天穿用千层底做得棉鞋,暖和、舒适还防滑。弟弟妹妹年龄小,母亲总是给他们的鞋上绣上虎头或是凤尾,做成虎头凤尾鞋。我则喜欢拉带的方口布鞋,母亲每次都满足我。冬天的棉鞋是五眼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就给我带了这样的棉鞋。只可惜,那时候我不懂得珍惜,害怕那些城里的同学笑话我,一直把那双鞋放在箱子里,没有拿出来穿。
昨天在报纸上看见一则广告,说是卖农家千层底布鞋。我给那个商家挂了一个电话,想买一双穿。我这个脚啊,自从穿上塑料底的布鞋以后,就得了脚气病。每一到夏天就格外严重,如今母亲去世了,再也穿不着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了。卖一双穿吧。一问价钱:280元。好贵啊!顶上名牌皮鞋了。商家说:我们的千层底布鞋是纯手工制作的,比皮鞋好穿多了!我哑巴了。我那亲爱的母亲啊,她一辈子做了多少千层底布鞋啊?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女儿要花280元买一双千层底的布鞋了。
在思念母亲的时候,我就想:中国母亲是多么伟大啊,他们勤劳又智慧,在那些物质贫乏的年代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做了多少双千层底布鞋啊!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抗日战场上那些八路军将士们脚上穿的不正是千千万万母亲制作的千层底布鞋吗?至今我还记得母亲给我们唱的《做军鞋》呢:“菜籽油点灯,灯光儿亮,庄稼人有了地脸上发光,一针针,一行行,吱儿吱儿得把鞋上,哎嗨哎嗨吆,我把它送到前线上。”如今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当年的八路军也成了各级领导了。我们怎么能忘记母亲的千层底布鞋呢?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儿,
站的稳那走的正踏踏实实闯天下。
最爱做的事是报答咱妈妈,
走遍天涯心不改永远爱中华。
这是九十年代解晓东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娃》中的两句,一双千层底布鞋,饱含着浓浓的思乡情。千层底布鞋,曾是农家女人必做的一项针线活。
春季,冰雪未尽的农忙前,母亲趁这个时候开始给做全家人的单鞋。千层底布鞋工序复杂,耗时长,一双单鞋最快也要四五天时间。
千层底布鞋的第一步是“打布壳”。母亲把所需的工具搬到院中,一张长桌,一笸箩废布(事先把废旧衣裤沿线拆开的布),一大碗浆糊,一把剪刀。先在桌上刷一层浆糊,铺一层布,剪去布料边角,再刷一层浆糊铺一层布,大概铺七八层,就成了。将长桌晾在院里,太阳暖暖的烤着。阴天里,就只好在屋里打布壳,打好后把桌子侧翻贴在火墙上烤,直到布壳干透。家里人口多,通常要连续打好几桌布壳才够做全家人的鞋。
接着是做千层底,母亲那张大床就成了她的临时工作台。拿出压在床头下的纸鞋样,鞋样分鞋底和鞋帮。把鞋样缝几针固定在布壳上,用铅笔描出鞋底轮廓,描完后拆下鞋样,沿铅笔印裁剪出来。一个千层底通常需要六七层布壳,摞起来要有一厘米左右的厚度。将每一层鞋底边缘用全棉白布条包一圈,用浆糊粘住,放置在顶部和底部那两层朝外的一面要全部用白布覆盖粘住,几层鞋底叠放对齐,顶部一针,底部一针分别固定好。以上工作仅是千层底的一个开端,接下来才是做布鞋最费力的一个阶段——纳鞋底,用大脚针穿上白色粗线绳,先用力把针尖刺入鞋底,再借助顶针使力将针穿透鞋底,翻到另一面,用钳子夹住针尖一侧,拔出针,连带抽出线绳,拉紧。纳鞋底,需针大线粗而针脚细密均匀,这样的鞋底漂亮又结实。
鞋底纳好后,做鞋帮。鞋帮只需依鞋样裁出一层布壳加一层条绒布,两层对齐缝合,鞋帮和鞋底连接的那一圈儿用白布条包边缝一周,鞋面处的边沿用黑布条包边缝合,鞋口处缝上松紧,使鞋面更加贴脚。再把鞋帮牢固的缝在鞋底上,这样一双鞋就完成了!
即便经济条件非常拮据,母亲也不会为了省布料而减少工序,做出的鞋,总是白净的鞋底,精致的鞋面和鞋袢,美观舒适又耐穿。有时赶得急,也会买塑胶或泡沫鞋底,这样就省去了纳鞋底的功夫。但只要时间充裕,母亲还是会一丝不苟的做千层底,并在款式、颜色和用料上都有独到的创新。在传统样式上稍加改动,就成了独一无二的新款,还会做全布制的凉鞋和拖鞋,鞋面上缝一朵旧头花,或旧裙子上拆下的装饰物;颜色和布料也不限于当时主流的红色或黑色两种单调的条绒布,桔的,粉的,绿的,碎布拼接的,有时鞋面上还会出现彩色丝线绣的一串梅花、一只鸣叫的鸟儿,或者是一丛花草、两只翩翩的蝴蝶。
最激动的时刻是新鞋快要做好的时候,眼看着母亲手中的鞋马上完工了,就守在跟前不肯走,耐心的等着缝完鞋帮的最后几针,钉好鞋袢的扣子,一双鞋递在我面前,“小娟,拿去试一下!”我飞快的找来纸铺在地上,脱掉旧鞋,才开始试穿新鞋。“脚拇指有点挤。”母亲接过我脱下的鞋,用钳子伸进鞋里,用力往前顶几下,再穿上时,就不那么紧了。新鞋一般都会有一点挤脚,但纯棉布鞋柔韧性非常好,穿一天就非常贴合脚部曲线,轻巧又舒适,还有着天然的透气性。
天暖了,脱掉笨笨的棉鞋,换上新单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新鞋只在上学的时候穿,在学校也避免跑动,一回家马上就换回旧鞋。春季化雪天,上学路上道路泥泞,为了护着新鞋不被泥水弄脏,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踮起脚尖蹦跳着选择下脚的地方,竟成了上学路上的一种乐趣!
小学时在大队上读书,同学们大都穿布鞋,五花八门,有的鞋面款式简洁,做工上省事,但穿起来不稳当,容易脱跟;有做工粗糙的,鞋底边沿没有包边,导致一圈线头毛边,不够美观;有图快而鞋底纳的针数不齐不足的,鞋底就容易磨损;有的只用塑胶底或泡沫底,穿起来不舒适且容易变形损坏;也有做工细致的,但从裁剪上看,怎么都觉得比不上自己脚上的那一双,常常暗自欣喜。从一双布鞋上,大致也能看出各家女主人是否勤劳手巧。
三两双单鞋可以从春穿到秋。棉鞋则是在农忙结束后的深秋开始动工。棉鞋的复杂程度远高于单鞋。鞋底是同样的做法,而鞋面就要多几道工序。鞋面上要絮上厚厚的棉花,还要锁鞋眼儿,工期就长得多。母亲通常会用整个深秋到冬季的.闲余时间做全家人的棉鞋。而过年前,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双新棉鞋。
读大学后,几个姐姐都已经离家外出工作了,母亲仍会在空闲时间做布鞋,就是为了我们回家那几天,能有布鞋穿。大二暑假回家,母亲得知我寒假要去二姐家,就提早做了两双布鞋给我和二姐。八月底,这鞋被我千里迢迢从新疆福海带到西安,又在寒假时从西安带到上海。最后一双布鞋,我一直珍藏着,毕业后几经辗转,竟不知遗落到了哪里。
几个姐姐嫁人了,母亲总会在外孙出生前开始准备一双双艺术品那样精致的小鞋子,等差数列一样,一双大于一双。遇到家人有谁去姐家的机会,就顺路带过去。我们一家人分散太远,新疆、四川两地相隔,鞋子带过去,也许孩子已经长大穿不了了。
如今,千层底布鞋已经成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制造业发达的今天,工厂生产一双鞋的成本远低于一双手工布鞋,大概除了部分农村,已经极少见到这纯手工的布鞋了。现在网上也有手工布鞋,部分被冠以“保健鞋”,赋予了中华文化的卖点出售。网上同时也有售布鞋加工机器,想来这布鞋也不会是真正的手工鞋了。
从小到大,不知穿坏了多少双布鞋。一年又一年,鞋码越来越大,母亲的风湿病却越来越严重,手指关节不能用太大力,手开始颤抖了,眼睛花了,穿针时总是瞄不准针眼,一双鞋耗费的时间就更长了。现在,皱纹深了,头发也花白了,母亲手里的鞋码又回归到几个月大婴孩的尺码。在不懂事的年龄,曾做过为了要新鞋,故意破坏旧鞋的事;有过为了让母亲买鞋,赌气不肯穿布鞋的任性;也有过对母亲做一堆看似没用的婴儿鞋的埋怨。这所有的叛逆、脾气和埋怨到了母亲那里,就像一股汇入大海的浊流,被无声地包容和净化了。
时常回想起母亲纳鞋底的模样,窗户边或煤油灯下,母亲左手握鞋底,右手捏针,专注地一针针穿梭着,不时用针尖划一下头发。我们姐妹几人像麻雀一样在房间里穿梭喧闹,却不曾打扰到母亲的安详。有时兴致来了,母亲也会听着收音机,哼着歌儿做活。一不小心,顶针一滑,针脚扎在手上,鲜血流出,用嘴吮吸一下,继续一针针的缝。
母亲瘦小的身子,是用怎样的力气把针穿过一厘米厚的千层鞋底?那时家里连一个纳鞋底用的锥子都没有,只能靠两只手的力量。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短小粗糙,每日操持家务,干农活,养猪鸡养牛羊,手掌已经是厚厚一层老茧,手指一道道裂缝里是洗不掉的黑色,还有几处新鲜伤痕。
现在少了孩子们的吵闹,孤灯下的母亲又在怎样的劳作呢?也许会想起我们小时候一些趣事,一个人笑出声;也许想起电视上看到的某个案件,对离家在外的我们产生担忧;也许会想还要给外孙准备些什么?想到这些,一定会忘记手中的活儿,一个人静静的长久的发呆吧。母亲将她所有的关心,叮咛,担忧,想念,期盼,一一收集起来,密密的纳入鞋底。
这千层底布鞋啊,层层思念,针针凝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