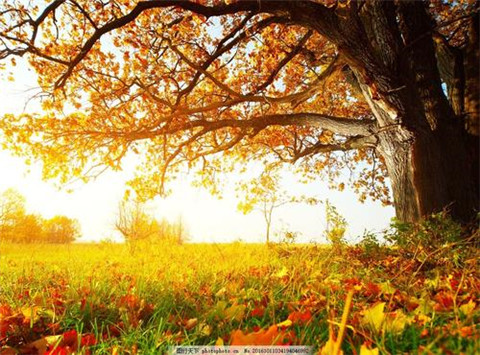他好像总是闲着,搬个小板凳,一个人默默在家门口抽烟。至于他的家,则是我所住楼下的一个简陋的地下室。地下室的门开着时,从外看俨然一个黑幽幽的洞口,带锈的铁门半掩着一个昏暗的空间。
有时天还是蒙蒙亮,他就会站在楼角发呆,皱巴巴的衣服裹在身上,粗粗的裤子风一来便没了形状。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吧,脸色如同糊灯的油纸一样,眼窝深陷,但眼神却是痴痴的望向西北角的天空。时间久了,就会再燃上一根烟,烟雾迅速笼罩了他那张冷冷的脸。
他抽的是那种自己卷的烟,我曾经看到过他装烟丝,烟丝掉在地上,他会捡起来,再次卷进细细的纸筒中。他抽烟是特贪婪的那种,仿佛不抽到火星烫到手指决不罢休。他好像没有手机,现代科技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影子。他也很少主动和人讲话,除了楼下的张大爷路过和他打个招呼,再就是无知的小孩子偶尔喊他一声“收渣货的”便飞也似的跑开,碰到这种顽劣的挑衅,他却还能难得的笑一下,然后依然坐在那儿宛如一尊雕像。
有一天,我忘了带家门的钥匙,无聊的走到楼下,站在楼房的转角处等爸爸回来。他一如既往的搬个小凳在门外抽烟,这时一只黑狗晃悠悠的路过,我向来是怕极了狗的,身体便不由自主的向他那边挪近了一些。他默不作声,也许没有注意我的动态,仿佛另一个世界的人。我有些尴尬。
黑狗没有离开的意思,时不时用那不善意的眼光盯我,我确实想寻求他的`帮助,于是,壮着胆子试探性的问:“您……您在这儿晒太阳呢?”他先将眼睛向上瞟了瞟,然后才抬起头,眼里有些漠然,我心里有些忐忑。唉,明知道他很古怪,不搭理他就好了。出乎意料的是,他说话了:“嗯,是的,你也晒太阳么。”声音有些沙哑,像枯叶摩擦的声音,但似乎也听得出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的心稍微缓和自在了一些:“不是的,我没有带钥匙,等爸爸回来开门呢。”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因为我无法从他的表情判定他的态度。他大概木然了几秒钟,站起来,把凳子给我,说:“嗯,你爸爸啊,我认得的,你好福气,有个好爸爸……嗯,你坐一下吧,站着累。”我犹豫了一瞬,终究还是接过了那把小凳子。太矮,我坐着都憋屈,估计他平时坐着更难受吧。
我们没有话说。
以为就会这样沉默下去,但没想到他突然开始对我说话,不,与其说是对我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我的老家好得很啊,空气好,那树叶子绿得可以掐出水儿来。”
我面对这样一句无厘头的开场白,接不上话。
“我家的玲儿应该也长大了吧,好想看看她啊。”他抽着烟,眼睛里是我从来没看到过的柔软。我不知底细,也不好说什么。
“本来说给阿芳买房子的……都三年多了吧……她们什么时候会来呢?姑娘,你看到她们来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我没有反应过来,只好顺着接了一个“嗯”。
原来,他有家人的啊,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单身汉呢。
他继续嘀咕着。长时间没有言语的人,一旦找到倾诉的缺口,就停不住了吧。
这时,爸爸回来了,我说我上楼了,他停住了话,向着我爸爸很不自然的笑了一下,然后恢复平时状态,木然抽着烟,木然出着神。他周围好像有一层薄膜,隔开了他和这个世界。
时间平淡的流逝着。
一天傍晚回家路过地下室,一个妇女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儿正在不停的敲那生锈的铁门,旁边放着一个竹篮子和一个鼓囊囊的旧旅行包,这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么?敲了半天,没人开门,那男人想必是出去了吧!那妇女满脸焦急,手不停的在衣襟上捏搓着,还不停的催那女孩:“你大声喊,看爸爸是不是在睡觉啊!”
过了许久,门没有开,也没人应声,她们放弃了。妇女四周环顾,看见了我,欲言又止,我也不敢随意发话。她又敲了几下门,还是没有回音。她回过头望着我,眼光犹豫闪烁了几下,还是开口了:“姑娘,你知道这屋里的人到哪里去了么?”
“不晓得啊,上午我出去的时候还看见他呢。”
“哪里去了呢?哪里去了呢?”
无语,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便准备上楼。
“姑娘,我从中午等到现在都没看到他……这个……能不能帮我给屋里这个人……我这……实在是……姑娘,你帮个忙,他回来了你叫他到舒安宾馆找我……”我接过篮子,沉甸甸的。舒安宾馆我知道,是街头很便宜的旅店。她还是不愿离去,我只好安慰说:“我会给他的啊。”她缓缓转身,还不忘回头交代:“这是鸡蛋,容易碎的啊!”我有些好笑,鸡蛋当然容易碎啊。她扯着那女孩,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小女孩还在不停的喃喃的问:“爸爸呢?爸爸呢?”妇女扯着她,也不答话,走几步,又回头看看那铁门。
满满的一篮鸡蛋,码得整整齐齐,这么多鸡蛋,应该是她攒了很长时间吧。我反正没事,就坐在地下室门旁那个小凳上掏出一本书慢慢翻阅。
许久,我听见了“吱呀”一声,铁门开了,我望过去,居然走出了那个男人!我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说刚才的事情。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门外发生过什么,只说了句“这是给您的吧”,就把鸡蛋递给他,他眼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光亮,隐藏着在深处的是更浓的悲哀。我终究忍不住,还是很小心的问他:“您,一直,在里面?”他摩挲着那些鸡蛋,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嘴唇嗫嚅着,发出模糊的声音:“……走啦……阿芳和玲儿都走啦……玲儿和你一样……好乖的……我哪有脸见她们……没出息……哪像个男人……我哪有脸哪……”
我有些手足无措,对于大人的故事,我很少去探究原委,更不用说是这样一个与我毫无瓜葛的古怪的男子了。我告诉了他阿芳住的旅店,他喃喃着,转身走进了昏暗的地下室。一会儿,他又出来,对我说了声“谢谢”,我赶忙“哦”了一声,不敢看他那张充满悔恨和自责的脸。
看着渐渐掩上的门,心中有一股酸涩。这个故事真实的发生在我眼前,却如同虚构一般。幸福的拥有,为何一定要和贫富挂钩?男人的尊荣,在逃避中岂能达成所愿?亲人最想要的也许只是你最朴实的相伴啊!
我无法评价他的对错,毕竟,这关于一个男人脆弱的尊严。
我能做的,只能是默默的祝福罢了。
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有雨,痴等了一天,也未能等来期盼中的清凉夏雨。
更夫在厨房准备晚饭的时候,室内异常闷热,很想冲个凉,解解身上的暑气。等一切准备就绪,却发现浴液已被两个大男人洗劫一空,手拿浴液瓶摇痛了胳膊也没能倒不出一滴。无奈,只好又穿戴整齐,准备去楼下超市“超”一瓶上来。
回来路上,听到有人叫我。隔着马路眯起眼细瞧,是以前同住单身的丽姐和兰妹。丽姐冲我喊道,没看到我们呀?还直蹦踉跄地往前走!我走过去,说道,不知道我这目中无人的毛病呀!我们这些在一起“鬼混”了十几年的姐妹见面就是这样,说话没个正经,而且口无遮拦,就连在这大街上见面打招呼,都让人听着特别刺耳。
也许是我们的说笑声大了些,引起了路人的关注,不时招来过路人异样的目光。这些异样目光也招来我们的关注,丽姐在过往的人群里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说,这位大侠(女侠)与某某是合作伙伴。兰妹问,他们合作什么。丽姐说当然是上下合作。兰妹晕,说不明白。正说着,大侠的合作伙伴某某也出现在人群里,紧跟大侠其后,向某个目的地走去。这时兰妹恍然,哦,原来是瓶子与瓶塞的合作。这个嘎妹,逗得我和丽姐忍不住在大街上又一阵好笑。
笑毕,丽姐说,咱单身出来的姐们,哪三块料凑到一块儿,都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戏言,感觉不是三个女皮匠,像是三个女流氓!
嬉笑间,眼睛向前扫了一眼。见不远处站着一位男士(用男士这个称呼,好像这个人不配,但为了不打击一大片还是这么用着吧),像是在一直注意着我们,在我眼睛扫过的一瞬间,他的手放到了“人”字的分叉处,还顺手拉开的“文明链”做了个很下流的动作。
想呕吐,感觉像是踩了狗屎,心里一阵阵直犯恶心。说自己是女流氓,不想青天白日的还真碰上流氓了。告知两姐妹,五大三粗的兰妹要过去抽他,吓的我和丽姐赶紧拦着。兰妹不依不饶,这等下流坯子,不见阳光的东西也敢亮出来,看不抽死他。我和丽姐连忙解劝,算了,就当是哪种穿着衣服的动物发情啦!
街灯亮了的时候,憋闷了一整天的天空终于下起了大雨。虽然是电闪雷鸣,但还是站在了阳台上,推开窗子,顿时有雨水迎面扑进来,还有清凉凉的风。迎着雨水,吹着凉风,嗅着水汽,身上舒爽起来,嘴里不由得随口说道:华灯初上,天降大雨,着湿了路人,却换得阵阵清凉。 更夫在我身后笑道:又开始发哪门子神经。
我被激怒了,冲更夫发了脾气。更夫像躲猪流感一样,溜走了。心中懊恼,发火不是因为更夫,而是因为刚才在街上被“羞辱”。
气消神定,拿起一本杂志,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他对我的激情只燃烧一次》。文中有一段话说的很经典:“……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你爱的人不爱你;而最最痛苦的事是,爱过你的人不再爱你,你却还在爱着他……” 世人一直用“水性杨花”来形容女人,其实文中的男人在对待爱情方面比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遇到这样的男人,面对这样的烦恼和痛苦,又有几个女人能做到带着理性去对待呢!除非她也是水性杨花。
记得友友说过,爱就是爱了,不要复杂化,要简单对待,别给自己太多的负担。很明了,这样的`爱是没有任何承诺和责任可言的。是在告诉别人,对待爱情时要做个水性杨花的人。
想起谁人说过的一句话:女人是睡的动物,男人是吃的动物。女人在爱的时候,是用心去投入的,把自己的未来憧憬在自己梦幻般的世界里。男人的爱像是在寻找食物,或者是猎物。饥渴了,需要拿食物来充饥。这种情景,让我想起在乡下时农民老伯的旱烟袋,想抽烟了,在烟斗中装上烟丝,点燃,狠吸几口,烟丝会很激情地燃烧起来,有时还能听到“丝丝”的声响。
这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即便是燃烧的再缓慢,其热度也维持不了几分钟,所以有“三分钟热度”之说。烟丝燃尽,轻敲烟斗,烟灰飞落,烟斗又变成一个待装的空斗。只是,何时成装烟丝,需要吸烟人自己定夺。
这瞬间的激情,很像是一种不需要承诺的爱情,想爱就爱了,激情过后,让燃烧后的灰烬随风而逝,不留任何痕迹!
想起一首歌,《飘摇》:“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如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轻唱这首歌,爱恨聚集心头。这歌词里分明在演绎着另一种生活,个中滋味又有几人能理解。受伤的人,伤痛的心,又有谁去慰抚!
在杂志的尾页看到一则幽默笑话:大象和蚂蚁结婚两天就要离婚,法官为其缘由。蚂蚁气愤地说,能不离吗?接个吻还得爬二十分钟!大象更气氛,说,是呀,接个吻还得拿放大镜找半天,还不能喘气!对原有爱情感觉平淡的时候,总想开始新的爱情,那种新奇的吸引往往无人能抵挡。然而,当新奇的爱情出现时,置身在其中,又真的能相互接受对方承受相互应承担的责任吗!
有一种玩笑说法:这世界上的男人女人分两种,一种是对爱认真的,一种是对爱不认真的。认真的和认真的在一起,不认真的和不认真的在一起,才能相互轻松,一旦错位,认真的一方非受伤害不可!细细想来,不无道理!
雨住了,开始还原于一个宁静的夜晚。
合上杂志,重又站到窗前,仍有阵阵清凉的风吹来。放眼眺望,远处有灯光闪烁,笼罩在雾气中,少去了往日的灼热,添了几许清凉。今夜,定是个清爽夜晚。
翻过这座山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了,他这样说道。他,时而幽默时而严厉,强大的自尊心导致了他阴晴不定的个性,泛黄的烟斗数落着逝去的岁月,一缕缕烟丝从烟斗上端植入,点燃,最后烟飞云散。强烈的二氧化氮弥漫着整个空间,安静的`气息使人窒息,我凝视着他的眼睛。他说:“等你再大一点就懂了”。
后来我真的在他的襁褓中长大了,他说:“你该出去闯荡闯荡了”,当他把房门关上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感觉缺失了些什么,眺望着天空,真的翻过这座山就可以到达我想要去的地方吗?眼睛似乎有些湿润,不敢敲开房门向他索取答案,似乎我真的很怕他,他那么庞大,那么强壮,黝黑黑的皮肤,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岁月的痕迹刮破了他原本就不和蔼的脸颊,仿佛多了几分威严。
现在我已经翻出了那座山,带着你送我的闯荡,翻出了那座,你告诉我只有越过它,就可以去我想要去的地方。可是,我发现他欺骗了我。无论我怎么行走,都走不到我想要去的地方。我疲惫的坐着山顶,呆呆的看着他,泛黄的烟斗咬的有些憔悴。
烟斗,你是否跟我一样在寻找他说:“翻过这座山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