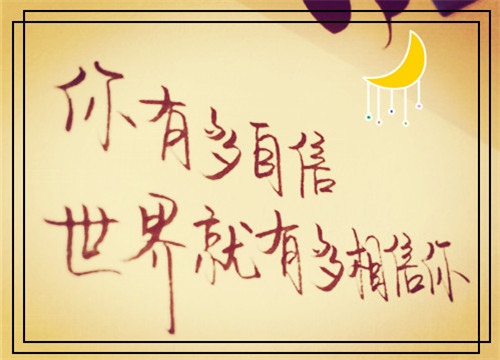
小街散文
小街,坐落在江南乡野之间。小街承载着我童年无数美好的记忆,哪怕时隔多年,小街的点点滴滴总在脑海挥之不去。
小街,虽说是条街,但却与一般人认识上的街有所不同。小街,严格地说来,那其实是一个村落。小街上的住户,除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有嫁到小街上的妇女外,那里的人都姓刘,是刘姓家族世居于此,说句毫不夸张的话,那街上的刘姓人五百年前铁定是一家。小街估摸着至少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江南典型的民居样式,都是青砖黛瓦,翘角飞檐,屋顶是那种有屋脊的坡顶,江南的民居都是以联排式为主,就是几户或几十户人家房子连着建造在一起,那种建筑样式,俗称‘搭山头’。当然独门独院的也有,但却是少数。小街,就是东西两排绵延二百米的联排民居,中间隔着窄窄的街,小街不长,却宽窄不一,最宽处五米多,最窄处也就三米的样子。小街都是青石板铺路,那石板经过百年雨水的冲刷,已经是光滑如镜,都能照出影来。小街上没有下水道,可即便是到了雨季,天天下雨,小街上也不会有积水。那是因为小街的地势是南低北高,是有一点坡度的,而小街的最南端就是一条河。哪怕是瓢泼大雨,落在街上,都顺势而下,流到河里去了。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出当年营造这条街的刘姓人的祖先的颇具匠心。街南端的河上有座桥,小时候我常在桥上玩高台跳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出去好远,才从水里窜出来,欢声笑语在小河里飘荡。本来以为那是条普通的小河,可有一次坐船出去走了走,才知道那条河居然是通江达海的,坐船可以东去上海,西去武汉重庆,北上京津,也可以去苏杭。
都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街也一样。小街毫不逊色于那些繁华闹市,小街上也是商铺林立。之所以对小街如此熟悉,是因为我姥爷家就在小街上。我母亲就出生在那里,我母亲也姓刘。姥爷家就在小街居中的位置,姥爷家对面是个杂货店,柴米油盐酱醋茶,店里都有得卖。我小时候常在杂货店里买些铅笔橡皮啥的',店里的售货员阿姨和我母亲很熟,很可能和我母亲是发小。我每次去姥爷家,售货员阿姨一看到我,就亲切地打招呼,问长问短,让我心里感觉暖暖的。姥爷家是个皮匠铺,姥爷是个皮匠。有句歇后语,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现在的90后恐怕都不清楚皮匠是干啥的了。皮匠其实就是做皮鞋的。当然也不是光做皮鞋,还帮人上鞋。啥是上鞋?这需要解释一下的。以前农村人穿的鞋大多是自己做的,布鞋或是棉鞋,做鞋都是先做底,再做鞋面,然后再把鞋面与鞋底结合起来,鞋就做成了。可鞋面与鞋底结合起来,这道工序都是由皮匠去完成的,也就是上鞋。以前姥爷家有大大小小几十个鞋模,那鞋模是用来给鞋子定型的。那些鞋模都是我儿时的玩具。姥爷家隔壁是个竹匠铺,一家三口,就靠编些竹席,竹篮等竹制品为生,那家人不是本地人,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外乡话。姥爷说,他们都是以前逃难过来的,日子久了,就在小街落户了。我闲来无事时,常去竹匠家看竹匠编席子。一根根薄薄的篾条,经纬分明,竹匠就靠把竹尺敲敲打打,半天功夫就敲出了张竹席。那娴熟的手艺真让人叹为观止。
小街上有个茶馆,茶馆里请了个说书艺人每天在那说书,所以每天来茶馆喝茶听书的人络绎不绝。喝茶用茶杯或茶碗,我想没人质疑。可是小街的茶馆里喝茶却不用茶杯,也不用茶碗,喝的是茶壶。茶壶,有嘴有柄有盖,大多是陶壶,考究一点就是紫砂壶了。茶客捧着茶壶,吮着茶嘴喝茶。茶喝少了,伙计就会来续水。茶馆里请个说书艺人,那是好个很高明的揽客手段。因为说书艺人说的都是长篇评书,啥【三侠五义】啊,啥【说岳全传】啊,一说就要好几天才能说完。茶客想要听完整的话,就得天天去喝茶。茶馆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说书艺人了。在离地半尺高的台上,台上有个齐腰高的书案,说书艺人就站在书案后说书。茶客喝茶喝的是茶壶,可说书艺人喝茶却用的是茶碗。这倒不是茶馆老板厚此薄彼,而是因为说书艺人是站着喝茶,喝茶壶不方便也不雅观。说书艺人说书是有道具的,一把折扇,一块醒木。旧时的县官审案手里有块惊堂木,如今的法官不用那玩意了,用的是一把小棰,叫法槌。法槌是用来维持法庭秩序的。说书艺人的醒木,也是那个理,底下听说书的茶客若有打瞌睡的话,艺人就用醒木猛击书案,震醒瞌睡虫。一把折扇,用处颇多,即可扇风取凉,也可充作大刀长矛。说书艺人说故事,假如说到三国里的关公了,那折扇就是大刀;说到张翼德了,那折扇就是长矛。说书艺人说书,绘声绘色,表情丰富,说到高兴处,手舞足蹈,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每到临结束时,艺人会一敲醒木,说一句,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小街上有理发店,也有中药铺,还有饭馆,裁缝铺,真可谓应有尽有。小街最南端有个剧场,经常是有草台班子来演戏的。江南戏曲种类很多,越剧,昆曲,锡剧,家乡民间演的大多是滩簧,滩簧也就是锡剧的前身。剧场不大,满座的话,也就五六十人的样子。戏曲演员在台上唱戏,也有华丽的戏服,也会甩精彩的水袖,也有委婉动人的唱腔,唱到紧要处,台下喝彩声连连。演员唱戏也有中场休息,中场休息也不会冷落了看客,会有两个说相声的来串场,说些笑话逗乐观众。也就在那一刻,剧场老板会出来讨彩。讨彩,就是讨赏钱。剧场的收入就是门票钱和讨彩钱。门票钱是必须给的,可这彩钱,也就是赏钱,你是看着给,你认为演得不精彩,就可以不给。当然很少有人不给的,和剧场老板都是乡里乡亲的,总要给点面子,多少也要给点。记得演出结束,演员回到后台,剧场老板马上递上两个生鸡蛋,那女演员把鸡蛋敲破一点,一吮就把那生鸡蛋吃下肚了。让我好生奇怪,那生鸡蛋是用来润喉的吗?还是用来补充营养的?时至今日,我都没想出合理的答案。
姥爷家皮匠铺的顶上有个阁楼,我每次去姥爷家小住,就睡在那阁楼上。阁楼临街,每天清晨天蒙蒙亮,街上嘈杂的声音就会惊扰我的清梦。原来小街还有菜市场的功能。小街附近村庄的农民每天一早就会把自家种的蔬菜拿到小街来卖,那菜水灵灵的,可新鲜了。小街上只有卖肉的,不是卖的自家产的肉。因为那时的农民,只要逢年过节才会杀猪宰羊,所以不可能天天有肉卖的。天天有肉卖的人,是肉贩子。小街互通有无,方便了方圆十里的乡亲。因而小街一直以来都是人来人往,煞是热闹。
小街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小街是我儿时的天堂。可惜小街早已不复存在了,小街所在地域如今是厂房林立,机器轰鸣。即便如此,小街时不时会在脑海出现,我会在记忆中咀嚼小街的一草一木……
小街优美散文
从我家楼宇走出,便是一条布满浓荫的小街——省会桥东区长征街,我每天从那里经过,久而久之,它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城市发展变迁的一道优美的风景。
小街过去是一条宽不足5米的小巷,两旁是矮小的平房,如今已变成洁净、宽敞的20米宽柏油马路,彩色方砖铺就的便道,再加上街旁两排葱绿、春花秋果的核桃树和林立高耸的高楼大厦,极富浓厚的现代都市气息。假如你曾经从她的清幽中走过,假如你经历过跌宕起伏的`生活,你一定会从心底里喜爱上她。多么好的一条绿色长廊啊!清凉、洁净、静谧、温馨、现代。
春暖花开时,小街上一株株的核桃树,暖暖的阳光照耀着,透过嫩枝、幼芽和新生的绿叶,一串串核桃花随风舞动,一树树风铃持续怒放,温馨的清香沁人心脾。没多久,绿满枝头的阔叶间,隐藏着的繁枝横向延伸开去,层叠粗壮,点点的核桃殷殷地探出圆鼓鼓的小脑袋,向行人点头致意,送来微笑。
在炎炎的夏日,酷暑难挨之时,远远地望见葱茏的绿影,胸中的暑热与浮躁先就退去了一半,待你走入其中,沐浴着清凉,昏倦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变得清健起来。
秋渐渐深了,雨丝飘过,风儿扫过,细瞅中,大树已是悄然换装,不经意间一种成熟风韵将那原本浓浓的绿意减淡了许多。天空柔和的光辉里,枝叶婆娑间,透过缝隙,有许多青果毫不引人注意地掩蔽其中,有的还很硕大,却也轻巧悬在枝头。
入夜,外出散步时,怀着轻松的心绪徜徉其间,感受着工作之余的那份淡然。橘黄色的街灯将小街当中照得亮堂堂的,而两侧的便道淹没在斑斓的树影中。在明与暗,光与影之间,流淌着宁静祥和的气氛,像有一层薄纱在翩然飘舞。清风袭来,送上阵阵清爽,虽是最平凡不过的微感,也会因它的到来,而入人心脾。
有这样一条洁净、静谧、温馨的小街伴我身旁,沐浴其中,陶冶性情,修正自我,是我莫大的幸运。
小街唯美散文
小街,坐落在江南乡野之间。小街承载着我童年无数美好的记忆,哪怕时隔多年,小街的点点滴滴总在脑海挥之不去。
小街,虽说是条街,但却与一般人认识上的街有所不同。小街,严格地说来,那其实是一个村落。小街上的住户,除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还有嫁到小街上的妇女外,那里的人都姓刘,是刘姓家族世居于此,说句毫不夸张的话,那街上的刘姓人五百年前铁定是一家。小街估摸着至少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江南典型的民居样式,都是青砖黛瓦,翘角飞檐,屋顶是那种有屋脊的坡顶,江南的民居都是以联排式为主,就是几户或几十户人家房子连着建造在一起,那种建筑样式,俗称‘搭山头’。当然独门独院的也有,但却是少数。小街,就是东西两排绵延二百米的联排民居,中间隔着窄窄的街,小街不长,却宽窄不一,最宽处五米多,最窄处也就三米的样子。小街都是青石板铺路,那石板经过百年雨水的冲刷,已经是光滑如镜,都能照出影来。小街上没有下水道,可即便是到了雨季,天天下雨,小街上也不会有积水。那是因为小街的地势是南低北高,是有一点坡度的,而小街的最南端就是一条河。哪怕是瓢泼大雨,落在街上,都顺势而下,流到河里去了。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出当年营造这条街的刘姓人的祖先的颇具匠心。街南端的`河上有座桥,小时候我常在桥上玩高台跳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出去好远,才从水里窜出来,欢声笑语在小河里飘荡。本来以为那是条普通的小河,可有一次坐船出去走了走,才知道那条河居然是通江达海的,坐船可以东去上海,西去武汉重庆,北上京津,也可以去苏杭。
都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街也一样。小街毫不逊色于那些繁华闹市,小街上也是商铺林立。之所以对小街如此熟悉,是因为我姥爷家就在小街上。我母亲就出生在那里,我母亲也姓刘。姥爷家就在小街居中的位置,姥爷家对面是个杂货店,柴米油盐酱醋茶,店里都有得卖。我小时候常在杂货店里买些铅笔橡皮啥的,店里的售货员阿姨和我母亲很熟,很可能和我母亲是发小。我每次去姥爷家,售货员阿姨一看到我,就亲切地打招呼,问长问短,让我心里感觉暖暖的。姥爷家是个皮匠铺,姥爷是个皮匠。有句歇后语,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现在的90后恐怕都不清楚皮匠是干啥的了。皮匠其实就是做皮鞋的。当然也不是光做皮鞋,还帮人上鞋。啥是上鞋?这需要解释一下的。以前农村人穿的鞋大多是自己做的,布鞋或是棉鞋,做鞋都是先做底,再做鞋面,然后再把鞋面与鞋底结合起来,鞋就做成了。可鞋面与鞋底结合起来,这道工序都是由皮匠去完成的,也就是上鞋。以前姥爷家有大大小小几十个鞋模,那鞋模是用来给鞋子定型的。那些鞋模都是我儿时的玩具。姥爷家隔壁是个竹匠铺,一家三口,就靠编些竹席,竹篮等竹制品为生,那家人不是本地人,说着一口我听不懂的外乡话。姥爷说,他们都是以前逃难过来的,日子久了,就在小街落户了。我闲来无事时,常去竹匠家看竹匠编席子。一根根薄薄的篾条,经纬分明,竹匠就靠把竹尺敲敲打打,半天功夫就敲出了张竹席。那娴熟的手艺真让人叹为观止。
小街上有个茶馆,茶馆里请了个说书艺人每天在那说书,所以每天来茶馆喝茶听书的人络绎不绝。喝茶用茶杯或茶碗,我想没人质疑。可是小街的茶馆里喝茶却不用茶杯,也不用茶碗,喝的是茶壶。茶壶,有嘴有柄有盖,大多是陶壶,考究一点就是紫砂壶了。茶客捧着茶壶,吮着茶嘴喝茶。茶喝少了,伙计就会来续水。茶馆里请个说书艺人,那是好个很高明的揽客手段。因为说书艺人说的都是长篇评书,啥【三侠五义】啊,啥【说岳全传】啊,一说就要好几天才能说完。茶客想要听完整的话,就得天天去喝茶。茶馆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说书艺人了。在离地半尺高的台上,台上有个齐腰高的书案,说书艺人就站在书案后说书。茶客喝茶喝的是茶壶,可说书艺人喝茶却用的是茶碗。这倒不是茶馆老板厚此薄彼,而是因为说书艺人是站着喝茶,喝茶壶不方便也不雅观。说书艺人说书是有道具的,一把折扇,一块醒木。旧时的县官审案手里有块惊堂木,如今的法官不用那玩意了,用的是一把小棰,叫法槌。法槌是用来维持法庭秩序的。说书艺人的醒木,也是那个理,底下听说书的茶客若有打瞌睡的话,艺人就用醒木猛击书案,震醒瞌睡虫。一把折扇,用处颇多,即可扇风取凉,也可充作大刀长矛。说书艺人说故事,假如说到三国里的关公了,那折扇就是大刀;说到张翼德了,那折扇就是长矛。说书艺人说书,绘声绘色,表情丰富,说到高兴处,手舞足蹈,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每到临结束时,艺人会一敲醒木,说一句,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小街上有理发店,也有中药铺,还有饭馆,裁缝铺,真可谓应有尽有。小街最南端有个剧场,经常是有草台班子来演戏的。江南戏曲种类很多,越剧,昆曲,锡剧,家乡民间演的大多是滩簧,滩簧也就是锡剧的前身。剧场不大,满座的话,也就五六十人的样子。戏曲演员在台上唱戏,也有华丽的戏服,也会甩精彩的水袖,也有委婉动人的唱腔,唱到紧要处,台下喝彩声连连。演员唱戏也有中场休息,中场休息也不会冷落了看客,会有两个说相声的来串场,说些笑话逗乐观众。也就在那一刻,剧场老板会出来讨彩。讨彩,就是讨赏钱。剧场的收入就是门票钱和讨彩钱。门票钱是必须给的,可这彩钱,也就是赏钱,你是看着给,你认为演得不精彩,就可以不给。当然很少有人不给的,和剧场老板都是乡里乡亲的,总要给点面子,多少也要给点。记得演出结束,演员回到后台,剧场老板马上递上两个生鸡蛋,那女演员把鸡蛋敲破一点,一吮就把那生鸡蛋吃下肚了。让我好生奇怪,那生鸡蛋是用来润喉的吗?还是用来补充营养的?时至今日,我都没想出合理的答案。
姥爷家皮匠铺的顶上有个阁楼,我每次去姥爷家小住,就睡在那阁楼上。阁楼临街,每天清晨天蒙蒙亮,街上嘈杂的声音就会惊扰我的清梦。原来小街还有菜市场的功能。小街附近村庄的农民每天一早就会把自家种的蔬菜拿到小街来卖,那菜水灵灵的,可新鲜了。小街上只有卖肉的,不是卖的自家产的肉。因为那时的农民,只要逢年过节才会杀猪宰羊,所以不可能天天有肉卖的。天天有肉卖的人,是肉贩子。小街互通有无,方便了方圆十里的乡亲。因而小街一直以来都是人来人往,煞是热闹。
小街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小街是我儿时的天堂。可惜小街早已不复存在了,小街所在地域如今是厂房林立,机器轰鸣。即便如此,小街时不时会在脑海出现,我会在记忆中咀嚼小街的一草一木……
《小街》的背后散文
新浪网发了短文《小街》,三天后,又把它转到了自己的空间日志。
原本安静如水的空间,很少有人光顾与问津,只因这篇不足两千字文章的涉入,现在竟红火起来,如同平静的湖水里投进了一块石头,涟漪不断。
看这篇文章的人,大都是我的同学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再就是曾经在矿区生活过的人们。也有很多网上不曾相识的朋友,赞誉声络绎不绝。其中有位朋友这样说道:
“感谢你让我们回忆起儿时很多趣事,我仿佛又看到能用三分钱买到一杯野酸枣。姐妹分享酸枣时的场景,眼睛有点湿润。因没有这三分钱,我们只能忍着被枣刺扎破手的疼痛,在山坡上或崖畔上自己去采摘……”
难道这篇文章真可以牵动大家对儿时的的回味吗?真可以给现已成人的朋友们以心灵的安慰吗?如此大的效应,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
我吃几碗干饭,只有自个心里明白。今天的社会,大学生到处都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在煤矿上呆了几十年,挖了一辈子的煤,没有见过大世面,已过天命的年龄,竟写起了文章,似乎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有时候自己在背地里还笑话自己,脸有时也会红,也会发烧,哈哈。难道别人不耻笑我吗?码砌文字不是件容易的事,又苦又累,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才可以。对《小街》赞誉的原因,我很清楚,不是我的文章写的好,只是赞誉之人,大都是在矿区长大的人。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被岁月冲走的记忆,在看《小街》的时候,无意间又重新唤起了他们对儿时美好的回忆罢了,不能说是我写的好,这是其一。其次呢?对于一个多情善感,喜欢怀旧的人;对于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心声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变成文字,利用网络的便捷,让那些迄今为止依然居住在矿区的人,和那些早早离开矿区,到外面打拼的人能看到这篇文章,不要忘记年幼时常常走过的小街,和儿时发小的感情,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忘记就是一种罪过,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金钱无法换来年幼时那种两小无猜,纯真的感情。每个人正是心中有着这样的情感,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才会有共鸣。
美好的东西应该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中,它是人生的一种财富。忘却了,丢掉了,都是一种损失。人们常说,珍惜现在,回忆过去,展望未来。这十二个字里面的含义,千言万语不能表白,只有用心去感悟了。佛家喜欢用一个“悟”字去告诫施主,看破不说破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是天机。
我在矿区学习生活的时候,伙伴们也经常打架,同学间也少不了斗殴。2011年6月,同学毕业三十年相聚,没有了踌躇满志的气概,只有老顽童般不老的快乐。谈论起过去那些令人脸红的事时,相互间竟大笑起来。过去所有的不悦和隔阂,在此刻的笑声中烟消云散了。满桌的佳肴很难看见筷子在上面舞动,只有手里的酒杯在碰撞,同学间相互诉说着在矿区的那些开心快乐的事。这次的同学聚会,起名为同窗情节。情节二字,道出了同学当初在矿区的生活写照,同时也讲述了我们这一代60后出生人的艰辛和快乐。
《小街》写的好与坏,自己无权也无颜去评判,读者才是上帝。我只希望自己的这篇文章,是一粒丹药,可以医治人们的健忘症。让所有看过这篇文章的朋友,能从中让唤起对往事的回忆,茶余饭后令你感悟童年的快乐就可以了。如果这一点你做到了,那这篇文章的作用也算达到了。在矿区长大的人们,一定会忆起自己春末夏初去捕蝉,夏日去潘家河游泳抓青蛙,回家的途中,也不忘捉几只大肚子蝈蝈,装在自己辛苦捡来的冰棍棍编制的笼子里养着,聆听蝈蝈在夏天的鸣唱……
一位同学朋友这样评论:
写的.细腻而丰富,它让所有走过小街的人的内心都有所颤抖,拾起那份质朴而单纯的灵魂,拾起那份珍贵的记忆,谢谢你!老同学!
如今,昏昏浩浩的生活让人的精神麻木不仁,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文章,需要这样的美好的精神食粮,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内心充满感恩之情。
是那个有小街的地方养育了我们这样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看到同学如此的评论,诚惶诚恐,深感内疚之情油然而生。我工作的地方很是偏远,难以和众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站不高,自然不能望远,局限了我的视野及思维,加上一支拙笔,不能很好地再现我们过去经常走过的小街全貌,心中甚是忐忑不安,唯恐文章发稿后遭到蔑嗤和奚落。一切还好,蔑嗤没有看见,奚落的语言未曾听说,定是朋友们看了《小街》后,念我也是矿区长大的乡邻,不去和我计较而已。谢谢朋友们的见谅。
再过几日,就是农历十月一日了。早清明,晚十月一,这话是祖辈们留下的,我知道该如何去做。去了,一定再在小街上走一趟,重温、感悟一下小街的温馨。虽说小街的路现在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有一个很亲切的名字——小街。这个名字的诞生,是生活工作在矿区所有人,心中默认的名字。这个名字,是矿区的一个标志;这个名字,现在依然在使用。
小街,你好,提起你,人们都知道你在哪,那就是在各自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