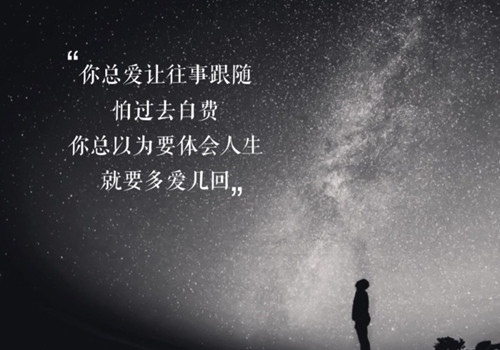贾平凹是一个高产作家,这缘于他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基础读者群,有人说他是偶像级的作家,他无论出什么书,都有读者乐于购买和收藏。
作品的艺术生命力长存于对读者的征服,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就有相应的想要了解作家生命历程和创作过程的读者。《贾平凹传》着眼于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生涯的追踪和关注,这本书会跟着贾平凹的丰富著作一路前行。
贾平凹是一个高产作家,这缘于他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基础读者群,有人说他是偶像级的作家,他无论出什么书,都有读者乐于购买和收藏。作品的艺术生命力长存于对读者的征服,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就有相应的想要了解作家生命历程和创作过程的读者。于是,就有了1990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率先推出的费秉勋的《贾平凹论》,以及1991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两本书,一个着眼于理论研究,一个着眼于创作生涯,这两本书跟着贾平凹的'丰富著作一路前行。
随着贾平凹的著作日丰,《贾平凹之谜》经过扩充,演变成1994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鬼才贾平凹》两卷本;其后,贾平凹年龄渐长,在前两本书的基础上再次扩大规模,7年后的2001年,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贾平凹前传》。期间,根据读者的需要,或某一专题,或某一时间,衍生出了几种单本的纪实文学。从2007年到2016年间,他先以长篇小说《秦腔》摘取了茅盾文学奖,接着几乎以每两年一部长篇的速度进入创作的喷发期。由孙见喜执笔的《贾平凹传》应运而生。
一是贾平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二是他的民间视角,这两点是贾平凹艺术大厦的重要支柱。
“贾平凹曾和刘心武等名家在上海《朝霞》杂志发表小说,以‘田园牧歌’享誉文坛,名声如日中天。读他的小说,总觉得是一个乡亲在同我说话。但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竟和我有着某种机缘,他父亲贾彦春曾当过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20公里,我们都是在丹江里光屁股耍水长大。20世纪70年代末,我和他开始通信并有了来往。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和贾平凹保持着频繁接触。我是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创作过程的见证人。”谈到与贾平凹的相识相交,孙见喜娓娓道来。
“要说贾平凹对我的文学活动有影响,恐怕主要在精神方面。他今年65岁了,出版的各种版本著作超过400种,这在当代文坛是独步的。况且他在国内国外获得过那么多重要的奖项,拥有巨大的读者群,他像一片翻卷着扩散着的狼烟弥漫在一处地域,外边的想进去闻闻是什么味儿,受不住的人会咒骂着逃离,沉浸其中的人又不能自拔。但我关注的是,他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及这种现象的成因。”有两点判断在孙见喜脑子里是明晰的,一是贾平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二是他的民间视角,这两点是贾平凹艺术大厦的重要支柱。之外,孙见喜认为,贾平凹的悟性和天赋,他的勤奋,他的敏于思、慎于行,经得住绊磕也耐得住挫折,保证着他文学之树的不断生长。或者说,正是他这种奋斗精神,感染着影响着他周围的文友和一批作者,当然也包括他本人在内。
正是基于此,基于对贾平凹的了解,对他文学作品的研究,孙见喜写作了《贾平凹传》。
以贾平凹的人生历程为纵,以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为横,立体地、多元地、网络状地再现一个文学生命的运行轨迹。
谈到关于《贾平凹传》的写作模式,孙见喜说:“我以贾平凹的人生历程为纵,以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为横,立体地、多元地、网络状地再现一个文学生命的运行轨迹。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叫生不立传,也有人认为,人活着尚未盖棺论定,所以不能为传。我说这是一种树碑立传式的传记观。成功者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一般都是曲折的,有的传主甚至后半生否定自己前半生的观点,有的还先是坏人后成好人。别人的写法是详写后边的辉煌,前边的稚嫩或错拙一笔带过,或只看后边的败坏抹杀前边的业绩,一切以‘论定’为标杆,我不取这种传记观。我的写法是前边的就是前边的,后边的就是后边的,互不替代,一切都应该充分而客观,唯一的标杆是要再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生命历程。”
孙见喜完成《贾平凹前传》三卷本用了16年时间。1984年秋开始写起,完成于2000年秋,全书120万字。写作这部书,孙见喜坦言,“一是出于感情;二是贾平凹的文笔最对我的口味;三是他笔下的商州生活、文化风俗我最熟悉,他将生活变为作品的过程,研究起来对我的创作有借鉴价值;四是贾平凹的文学天赋。贾平凹1985年一年发表了10部中篇小说,1992年到2000年不到10年时间,他创作并出版了5部长篇小说,这个事实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创作的量;在质上,他的独步无人替代,他追求小说中国化的意义深远,他参与了新时期一些重要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创立及推动;这些事实证明了我的‘冒险’是有意义的。作家的所谓声誉,全来自读者,读者不认卯,挣死也没用。”
贾平凹还在写作中,还在行走中,还在他钟爱的乡土挖掘和捡拾着文学的养分,所以,贾平凹必然还会有新的著作不断地奉献给读者。
这一夜,光子睡不着,看了一夜窑窗窟窿里透进来的月光,听了一夜窑外的蟋蟀声。虎娃爬起来,瞧爹的眼睛光光的,说:“爹,你也没瞌睡?”问话问得奇怪,光子说:“没瞌睡。”虎娃说:“你也想着那个婶婶吗?”光子久久地看着儿子,心里发酸,问道:“婶婶好吗?”应答是:“婶婶好。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光子赶紧催他瞌睡:“信嘴胡说,你能在哪儿见过?睡吧,睡吧!”
虎娃睡着了,他却直感到命运竞这样捉弄他!他同情亮亮的遭遇,却又害怕同亮亮结婚,当年亮亮和拉毛,是自己侮辱了他们,拉毛才身亡的,如今自己却要同亮亮结婚,虽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但心里总有一个阴影。自己是什么人,农民,最窝囊最不景气的农民,怎么能要一个教师的女儿?亮亮虽然坐过牢,但她已经平反了,她是可以找着比自己更强的人的。他是不敢再见着亮亮,也不能对媒人说明原委,天未明就将虎娃摇醒,收拾了全部家当,拉着走了。虎娃说:“爹,咱这到哪儿去呀?”他说:“这儿不是咱久呆的地方,回到老家去吧。”虎娃再问:“那个婶婶也和咱走吗?”光子说:“你没有那个婶婶的!”拉了孩子却去了白水的坟上,父子双双跪下磕头。他们一直往东走,白日吆喝着给人劁猪骟驴,到谁家,也不收费,只求管饭,黑了就睡在谁家。如此半月过后,还未走出洛南县境。一日到县城,父子俩正蹩行街头,忽啦啦一群人往东跑。光子不知有了什么事,问时,说是“去看热闹呀!”光子问:“什么热闹事?”那人说:“有一个女人,天天到县委来告状,书记被她找烦了,再不见她,后来连门房也不让进,她又吵又闹,是个神经病哩。”光子也就不再问下去,到一饭店去吃饭。吃着,虎娃却出去了,再找没有找见,急得光子满头大汗,虎娃回来了,说是他去看那神经病人去的,就附在爹的耳边说:“爹,那神经病人我认得呢!”光子问:“认得是谁?”虎娃说:“就是那个婶婶。”光子脑袋嗡一下,浑身麻木,他万万没想到,亮亮会是这样,一个肥胖症的独身女人这么告状,她住在哪儿,吃在哪儿,一肚子委屈又会向谁诉呢?光子在心里骂自己:“光子,你一辈子干些啥呀,亮亮之所以要找个家,就是有个落脚,好为上告申诉,你却又不言不语走了,这女人已经苦了半辈子,第二天再去找你时,那心里会怎么个想法?便对虎娃说:“走,领爹去看婶婶!”
去时,人已走散,亮亮也无踪影。问门房的姑娘,姑娘说:“神经病,谁知道住在哪儿,天底下还有这号没脸面的女人,才出了狱,寻着又要进狱哩!”旁边有人说:“我知道她住在哪儿。”光子就拱手打问,那人说:“谁也不收留她,她去联合那些坐过狱的人一块儿上告,却被人家笑骂了一场,说她无事找事,不肯让她住,怕再连累。她白日四处找各位领导,夜里就睡在城关七队的看庄稼的庵棚里。”光子道了谢,一就—一路寻城关七队的庵棚。庵棚没门,里边果然有一床破被子,像是人睡过的,但亮亮没有在。光子流了两股眼泪,对虎娃说:“虎娃咱让婶婶和咱们一块儿走行不行?”虎娃说:“行的。”光子又说:“你以后愿意叫她是娘吗?”虎娃说:“我娘已经死了。”光子说:“你亲娘死了,她就给你做后娘,你叫不叫她?”虎娃说:“叫的。”父子俩默默坐了一会儿,光子就让虎娃在这儿等着,他去买了几个饼子。赶回来,虎娃已经在亮亮的怀里睡着了,光子叫声“亮亮”,两人相抱,悲痛欲绝。
光子父子从洛南往回走,同行的从此有了亮亮。他们没有结婚手续,但光子作丈夫,亮亮也作了妻子;虎娃跑前跑后,叫一声“爹”,就要叫一声“娘”。一家三口沿途一边儿做手艺,一边儿混嘴赶路,早起晚归,历尽辛苦。光子说:“亮亮,这状是告不倒的,那些人当年制的冤案,现在寻他们告,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咱们回去,将家安顿了,我陪你,咱往上边告,省上告不赢,往中央告!”亮亮说:“有了你,我心里也踏实。一个女人,遇着大事,心里也是没个主见,我为了告他们,是没个主心骨,没个知我疼我的,天黑睡在那庵棚里,半夜半夜地流泪。你娶了我,你不嫌弃我不安分吗?”光子说:“这么大的冤案,我怎能不让你上告?他们作践你是神经病,我看你是比男人家还强哩!我是穷光蛋的人,那天虽偷偷走了,我是嫌我配不上你,没想你……”亮亮也流了泪,说:一日月把我折磨得也男不男、女不女的,一个女人家,谁没有自尊心?可我不那样做,我这心不死啊!咱们穷是穷,总算是…家人了,我相信这案子能翻,恶人会得到惩罚的,到那时,咱的日子是会像人一样过的。”
到了商南,村人皆惊奇,说是光子出去一趟,竞发了,领回来一个老婆。亮亮在村里,劳动不行,又会吃烟,动不动又发大火,又爱认个死理,村里人就又议论她不像个女人。后来知道她是才出狱的,又四处告状,就拿冷眼看她。光子出外,村人就说:“光子,什么人不可找,偏找这号女人,她坐过牢狱,什么也不怕了,能好好跟你过日子?”光子只是不反驳,回来也不对亮亮提说。买了许多纸,夫妇两人在家写状子,光子文化浅,不会写,夜夜就守着灯看着亮亮写,自己拿了鞋耙打草鞋。稻草拉动索索地响,亮亮写不下去,他就笑一声,独自拿了到院子去打。半夜了,亮亮说:“你歇着吧。”光子坐炕上,亮亮将写好的状子念给他听,某一处说得太重,他说:“话不能这么说,当官的也是人,咱不能一笼统说怎么坏,要告咱就具体告县上那几个制造冤案的人,上边必然会下来调查,一调查了咱再说。”亮亮连连点头。可是,状子接二连三寄到省上,却泥牛人海,没有消息。
亮亮又去洛南询问。那做头儿的说:“你问状子吗?状子在我这儿。你就是告到天上玉皇大帝,还是批下来让我们处理的。”亮亮回来只气得呜呜哭。光子见女人恸哭,心也软了,好劝说歹劝说,亮亮只是哭得厉害。光子说:“你是刚强人,怎么一下子软成这样?”亮亮说:“我也不知道,以前遇到什么样的事,我都从未哭过,自从嫁了你,不知道这眼泪就这么多了。你说,现在咱怎么办呀?”光子说:“省上告不成,咱往中央递状子。”夫妇就上书北京,每隔十天寄一封出去。亮亮已经在村里住过五个月,苦苦焦焦的,身子不但没有瘦,反倒越发肥胖。渐渐天气转凉。
到了冬日。一日窗外雪雨潺潺而下,光子和亮亮拥坐在火炕,光子忽问:“你没有什么感觉吗?”亮一亮脸色泛红,摇头不语,后来说:“光子,你也是这把年岁的人,我知道你盼有个儿女,这么长时间没个身子,我害怕是这病的原因呢。”一脸羞愧。光子就安慰道:“不会的,你是会有个儿女的,你爹娘死的惨,你上无兄,下无弟,我并不是一定要你给我生个儿女,我想你们这一宗门也不至于从此就没了后代。”话这么说着,又过了数月,亮亮还是没有任何迹象。到了七月十五,瓜果成熟,晚上亮亮上炕去睡,觉得有硬硬的东西,揭了被看时,竟是一个大北瓜。问光子是怎么回事?光子只是含笑不语,问得紧了,说:“是给你偷娃呢。”原来此地风俗,不孕妇女到了七月,村里好心人就从地里偷了瓜果悄悄塞在其妇被窝,这样可祈望怀孕。光子前几天就让村里人给亮亮偷一次“娃”。村人嘴上答应,实际并不肯干。光子就自己从自留地摘了北瓜,塞在自己炕上。亮亮听了原委,先是嗤嗤笑,后来抱着北瓜则嘤嘤抽泣,说她全是这病得的,以前和拉毛,不该生育时倒生了一个女儿,如今成心要生了,却生育不下。光子就说;“拉毛留下的那孩子现在不知道活在世上不?可怜这孩子命苦。”自此亮亮更更待虎娃好,家里好吃好喝的全让他吃。虎娃也乖巧,将“娘”叫得很甜。
又是一春,告状依旧没有消息。亮亮说:“与其咱们这么在家死等,不如让我亲自去跑一趟,到北京去!”光子说:“你这是疯了,你知道北京在什么地方?”亮亮说:“鼻子下有嘴,我可以问着去,到了北京,就寻那天安门,北京人还能不知道状在哪里告吗?”光子说:“那要多远的地方,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亮亮说:“我怕这连累了你,这次告不赢,或许我还会坐牢的。你还是在家吧。”夫妇两人就四处筹钱。光子为人家劁猪骟驴,几个月里家里不见油水,如此省吃俭用,积攒了百十元。百十元哪儿够盘缠,后来他就上山去砍荆芭卖,他心重,别人一次背百十斤,他背二百,分两次,一百背下山了,再上山背另一百,然后一路反复倒转,天黑严了才能回来。亮亮身子笨拙,行动迟缓,就和虎娃找着公路养路段,为人家砸铺路石。用竹子编一个圆圈,套了石头,举锤子砸,母子天不明就坐大路边,直砸得满天星月方回。村人皆议论:这一家浪子回头了,像个过日子的人家了。再见着光子,便说:“你们夫妇若早早这样,日子早也富了!”光子说:“我们在攒钱,有了钱再去北京告状呀!”村人说:“还要告状?”再要告,就会家破人亡的。人是要安分,农民嘛,还想怎么的?亮亮得了五百元还不足数吗?”光子说:“这你不懂。”村人说:“不懂,我不懂?我看你娶了那女人图了啥,一不能生娃,二不能劳动,就是陪她告状?”越发认为光子是傻子。
阴历七月,虎娃六岁,夫妇双双送去上学。这孩子极尽聪慧,四岁上就开始认字,认得百位以下数目,五岁上有亮亮教授,能背得十首
两人背了一卷铺盖,又烙了石子饼带上,一路不敢住大旅社、下馆子,讨水泡了石子饼充饥。石子饼是乡里特产,将面团揉到醒透,擀出薄纸一般,放洗净的石子在锅烧热,面饼摊上,再履一层热石子所作。如此有车扒车,无车步行,走了半月,到了郑州,亮亮已经精疲力竭,坐在火车候车室里不能动弹了。其时天还热,候车的人多极,光子说:“我打问了,咱如今方走了一半路程,你就病成这样,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北京?还是买了票,坐火车走吧,一问,车票每人十几元,亮亮就心疼,说:“咱不是到北京事就完了,听人说如今上告的人多,全都到北京来,要在国务院门口坐了长队等候,十天八天或许不行,一月两月也说不定。咱们到了那时,没了钱吃什么,花什么?”急得光子挠头抓耳,苦无良策,买了两杯水就石子饼来吃。亮亮说:“这鬼地方,什么都是要钱,咱老家水用井盛着,这儿一口水也值得花钱来喝。”候车室人都带有干粮却差不多全坏了,瞧见光子他们吃石子饼,顿觉稀罕。问是几时烙的,亮亮说:“二十天前。”众人愕然。亮亮就让他们品尝,尝者莫不叫好,就有人掏钱来买。连光子也未想到,十三张石子饼竟卖得二十三元,两人喜不自禁,便买了车票,一天赶到北京。没人处亮亮哈哈大笑:“石子饼救了咱们,往日都说城里人捉弄乡下人,倒是咱乡下人捉弄了城里人!咱也尽量不吃这饼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卖个好价钱的。”
西安街头,艺人很多,有玩猴的,有弹唱的,有运气划拳的,有行书描画的,一帮一伙,很是热闹;常常这伙拉了那帮观众,那帮又搡了这伙生意。于是,得胜的坐地不走;败下阵的',悄遁而去,暗中再苦练绝技,又来挤垮别人。一时间,你争我斗,技愈来愈绝,观众却愈看愈馋,水涨船高,不亦乐乎。忽有一日,从南方来了一伙耍蛇人,展出七寸蛇、双头蛇、眼镜蛇、响尾蛇、大蟒蛇,白、褐、赤、青,色彩斑斓,便声名轰然满城,围观者匝匝而来,如潮汹涌,经久不衰。
耍蛇者一共五人,一老者,两壮年,另有一婆一女,俨然一户人家。先是白布围了四周,宣称日耍五场,每场定时,人不足三百则等,人过三百则谢绝不卖;观众觉得稀罕,购票的队列长达几十米远。进得场去,四边排列大小不等的名蛇近百,皆是玻璃箱罩,蛇在里边有蜷,有卧,有蠕,各尽其态,观者森森然不忍看,却又不忍不看。
“锵咚”一声锣响,耍蛇人在场中摆出台子,口若悬河地大讲蛇的丑恶、凶猛,使人毛骨悚然。说罢,便打开身边一个木箱,掀去外层木板,显出一个铁笼,内盘两条大蛇,一条青绿,一条灰黄。两蛇先十分亲昵,扭成一副绳状,然后作恶起来,各自绕成一团,头伸向上,相持相搏,如斗鸡一般。忽丢进两只灰鼠,蛇双目鼓出,勃然而起,囫囵吞下,便见蛇身凸起拳大一包,从蛇身上部蠕蠕而下。随之,又丢下一鼠,两蛇相争,一衔鼠头,一咬鼠尾,互不谦让,鼠便裂为两截,殷血流出。
观者倒抽凉气,面如土色,牙齿咯咯磕打,正欲退步,又一声锣响,蛇箱覆盖,耍蛇人又哗啦打开一大木箱,观众不知又有什么恶蛇出现,正疑恐之际,箱中却冉冉开出一朵鲜花,花枝分开,露出一张俊俏小脸,流目盼顾,含情脉脉,竟是一风流少女。观者为之一筋骨放松下来,随即就报之一笑了。忽然,一蛇跃上,蛇首与少女几乎平肩,观者一惊,顿时毛发竖起,一颗心悬在喉间。那少女无动于衷,任蛇缠绕身上,匝匝如背绳索。蛇头翘在脸前,少女目光凝视,嘴唇翕动,似作窃窃私语。忽蛇头一动,观者大惊,那蛇便钻入衣内,头从领口探出,立时缠脖颈,愈缠愈紧,少女面有难色,做出万般挣扎苦状。观者惊骇不已。少女却用手轻揉蛇身,微握七寸,便慢慢附过嘴来,竟在那蛇头频频亲吻呢。观者失声惊叫,有拥近去似要解围的,有纷纷后退欲要逃走的,有呆立原地,口不能言,步不能移的。那少女双眉颦起,猛握七寸,蛇哗然绽脱,她便双手托起,又在手中万般作弄,或掬或握,或作衣带系腰,或作围巾缠头,末了,提起蛇尾,蛇直直下垂,如棍,如绳;少女则一声嬉笑,低头向观众致意,头上鲜花酥酥颤动。
此时,观众方从惶恐中醒悟,嘘出一口气来。有人便炫耀道:“再往下看吧,还有老太婆表演人蛇生死搏斗哩。”锣又响起,宣布绝技轮渡演出,本场结束。观者终未看到人蛇生死搏斗,掌声仍是骤然爆起,纷纷再丢零钱,场中一时镍币闪闪。
演毕,有好心人围住少女,塞上一把票子,且问:“你这么年幼,聪明俊美,为什么要干这个吓人行当?”少女说:“今人不以自然为美,游园要赏荷花,登山要观怪古,我们耍艺的,只好如此。”说完,长叹一声,令人感慨。
附贾平凹人物介绍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当代作家。[1] 2017年3月22日,澳门大学向贾平凹颁授了荣誉博士学位。[2]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3] 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8年凭借《满月儿》,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4] 1982年发表作品《鬼城》《二月杏》。[5] 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创作《废都》。2003年,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6] 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7] 2011年凭借《古炉》 ,获得施耐庵文学奖。